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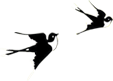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刘墨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刘墨 > 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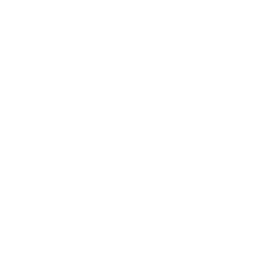
时间:2017-04-19 02:11:30
在西方人眼中,鹤是飞禽,虽然它在中国的科学分类中,也是如此,然而中国古人却愿意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仙”字,把它叫作“仙鹤”,这样一叫,它的来历就非同寻常了。
神仙二字虽然全称,但解析一下,西方人重“神”,中国人重“仙”,因而中国人所说的“神仙”,实际上是“仙”,因而它的文化里,不像西方人那样重彼岸的超越,而是人间生活中活得有“仙意”、“仙气”。
神仙,有人的有情,同时又有人所不能的无情,因而它是一种有情又非有情的状态,与道家圆教义理相通。判断一个人有“仙风”,或者“凡庸”,其区别亦在于此。
比如北宋的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正以其是在人的有情和非常人所有的不情之间,见其高尚处。
以梅为妻,其来源或者在于冠以柳宗元之名的《龙城录》一书,虽然这本书并不真的出自于柳的手笔。故事是这样的: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傍舍,见一女子淡妆素服,出迓师雄。时已昏黑,残雪对月色,微明。师雄喜之,与之语,但觉芳香袭人,语言极清丽。因与之扣酒家门,得数杯,相与饮。少顷,有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亦自可观。顷醉寝,师雄亦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久之,时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尔(《龙城录》卷上《赵师雄醉憩梅花下》)。故事的美丽与令人追忆,就在于赵氏与梅花仙子的感情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普通男女之情,哪里会有这样清微淡远?要么比它多情,要么比它无情,所以与其说这段故事体现了赵师雄与梅花仙子间的深情,倒不如是体现了一种若有若无的“仙意”更为合适。
有了这样的襟怀,鹤的高致也才能展现出来。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牵涉到神仙思想或道家对待物与情的态度。艺术,面对的不正是此情此物吗?
道家以无为本,人性与艺术都属“有情”,因而应该化去。《老子》第一章谓:“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个“徼”字,《老子》全书只出现了一次,河上公这样解释:“徼,归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观世俗之所归趣也。”因而“徼”的含义极其难以确定。不过,大致的意义是,“有欲”以“观其徼”,是站在“有”的角度上观察人或肉身的有为、造作,而如果人在此中,就只有有限性,从而失去物自身这一意义。所以老子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其意味也就说明,没有肉身造作出的徼向与轨辙,人就不在条件制约限制之中,此时我与物皆可得物自身的身份——“无”,照显出了人性的超越层,“无”掉的是经验有限层,是世俗。
以“无”为本,以“有”为用,这属于功夫修养。在“无”与“有”之间的圆融相通,就能到得“妙用”,不溺于一极,因而时时能见于道。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传统艺术家总是将为艺等同于“修道”——应物之时有对意志高度的磨砺,而道无物不能应,意味着修道时时处处皆可。所以中国人即生活即修道,只需在日用平常中体会到一种与物俱化的“仙意”,无需在日常之外另设宗教。
在中国典籍中,有一本《相鹤经》,年代不容易考定,一般题作明人周履靖所辑,但内容却是有趣的。
鹤者,阳鸟也,而游于阴,因金气依火精以自养。金数九,火数七,故禀其纯阳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黑毛易。三年,顶赤,为羽翮。其七年小变,而飞薄云汉。复七年,声应节,而昼夜十二时鸣,鸣则中律。百六十年大变,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茸毛生,乃洁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或即纯黑,而缁尽成膏矣。复百六十年,变止,而雌雄相视,目睛不转,则有孕。千六百年,形定,饮而不食,与鸾凤同群,胎化而产,为仙人之骐骥矣。
夫声闻于天,故顶赤;食于水,故啄长;轩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周;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且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故天寿不可量。所以体无青黄二色者,土木之气内养,故不表于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屿,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清崇者也。
王策纪曰:千载之鹤,随时而鸣。能翔于霄汉。其未千载者,终不及于汉也。其相曰:瘦头朱顶则冲霄,露眼黑睛则视远,隆鼻短啄则少暝,鞋[故解反,又音谐]颊宅[得宅反]耳则知时,长颈竦身则能鸣,鸿翅鸽膺则体轻,凤翼雀尾则善飞,龟背鳖腹则伏产,轩前垂后则能舞,高胫粗节则足力,洪髀纤指则好翘。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皇翔于郊甸。
其经一通,乃浮丘伯授王子晋之书也。崔文子学道于子晋,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八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世。
又有所谓《相鹤诀》者:
鹤不难相,人必清于鹤而后可以相鹤矣。夫顶丹胫碧,毛羽莹洁,颈纤而修,身耸而正,足臞而节,高颇颣不食烟火人,可谓之鹤。望之如雁鹜鹅鹊然,斯为下矣。养以屋,必近水竹。给以料,必备鱼稻。蓄以笼,饲以熟之食,则尘浊而乏精采,岂鹤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候其馁,置食于阔远处,拊掌诱之,则奋翼而唳,若舞状。久则闻拊掌而必起此食,岂若仙家和气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种恐未易得,惟华亭种差强耳。
这样的种种说法,如果以是否符合科学来进行判断,那未免太唐突了人们的想象。有想象的地方,才有梦想。有梦想的地方,才有艺术。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了。
古人于鹤,有名的故事太多,对我的印象,一是传为陶弘景所书的焦山《瘗鹤铭》,一是唐朝薛稷的画鹤,一是林和靖的梅妻鹤子,一是苏东坡的放鹤亭。四段故事,为画鹤增添了无限的文化内涵。其他的鸟类,似乎还几乎没有如此深厚的人文内容的。
如今画鹤的人多了,但画鹤的始祖,似乎应该追溯到唐代初期的薛稷。他的作品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只能从历史文献中追想一二。对古人来说,画鹤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宣和画谱》卷十五记薛稷的画时提到:“且世之养鹤者多矣,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为之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氅之黳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又至于别其雌雄,辨其南北,尤其所难。”
我的忘年之友曹无喜欢画鹤,且近来以鹤为主要创作题材,佳作迭出。他不止一次和我说起过他画鹤的经历。为了画鹤,他南来北往,细致研究鹤的种类、习性、形状,避开历史上的图式,直接面对东西南北的野生鹤群,观察之、纪录之、研究之,发而为画,全不蹈袭前人,画面生新流动,至为可喜。
我仔细观察过他的画面,鹤的眼睛、喙、爪、羽毛,或飞或立,或行或站,无不依据真实的鹤的结构而为之,但是,曹无画的是中国的大写意,而不是来自西方的油画或水彩,因而他虽然在画鹤的时候采取了写实的手法,但在背景的处理上,他又回到中国画的写意传统,纵意所如,深得无人深处的烟水空灵之状。此是仙意抑或画意,还是留给观者去体会吧。
(刘墨,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