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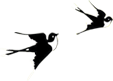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焦点新闻
当前位置:首页 -- 焦点新闻 
命运墨皈
梁占岩 袁武 张江舟水墨艺术展
八大美院巡展第一站
▼
主办单位
天津美术学院
学术主持
王鲁湘
承办单位
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
艺术百年
▼
展览时间
2017年5月18日—30日
展览地点
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
▼
展览开幕
5月22日 15:00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天纬路4号

命运墨皈
——梁占岩 袁武 张江舟水墨三人行
文/王鲁湘
把梁占岩、袁武、张江舟三位当代水墨人物画家集结一起,做一次历时四年的八大美院“三人行”,是一个大胆而有趣的想法。
这个想法,由朦胧到清晰,有一个过程。人们一定会问:
为什么是他们三人?这个组合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要取“命运墨皈”这么一个艰涩的名字?
壹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梁占岩,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执行院长;当代水墨人物画家。
袁武,北京画院原执行院长;当代水墨人物画家。
张江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当代水墨人物画家。
三个人都是长期在画院工作的职业画家,而且都担任过画院的领导工作,不仅自己搞创作,还主抓过院里的创作,是一个不仅自己画画,还管别人画画的画家。强调这一点不是炫耀他们的“权力”,而是中国有这样经历的画家为数很少。这样的经历,势必对他们个人的创作产生影响。
画院体制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是大一统政治在美术领域里的制度保证,是国家意志在美术领域的执行机构。尽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运行以来,一直有人诟病甚至激烈攻击画院体制,但它依然屹立不倒。原因很简单,只要中国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个自20世纪50年代恢复并建立起来的画院体制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当下中国的美术生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三国演义”。
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市级的专业画院。画家吃财政饭,没有教学任务(创收教学的各种培训班不算),只需专心创作。
二是从教育部直属的八大美术学院到各地师范学院的美术系,其教员有教学任务,这是硬性的;也从事创作,这是软性的,因此美院系统有许多老教师一生从未搞过象样的创作,却留下许多素描、静物乃至风景写生的课堂教学作品。但也有许多教师是美术创作的主力,中国许多著名画家是在美院,边教学边创作。
三是那些不在这两大国家美术体制之内却以美术创作谋生的职业画家。他们大部分受过美术院校的专业教育,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跻身以上两大国家美术体制之中,只能在艺术市场上生存。在这个画家群体中,有一部分画家是因为观念上的不同而主动采取了从国家美术体制中自我放逐的方式,甘居于体制之外,选择了自由画家的道路。
梁占岩、袁武、张江舟三位画家,进入画院体制的个人道路或有不同,但都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凭创作实力和作品,被选调到专业画院。用美术界的话说,他们不仅是特别能画的画家,而且是特别能搞创作的画家。而这,恰恰是画院对画家的唯一要求。相较而言,美术院校对教师的要求,当然是要能画,但创作能力的要求就不会这么强调了,更何况,基础教学更要求教师安心于课堂,教学工作会分走很多时间。就投入创作的时间来说,画院画家较美院教师更具优势。
但是,美院教师的美术创作可能更具学术探索性和纯粹性,因为他们的创作会更多地从教学相长中产生问题意识,在学术探索的校园气氛中产生先锋意识,相对封闭的“象牙塔”环境,自然会引导他们更专注于语言与形式的创新。
而画院画家的创作,对题材的社会性、历史性和主题性的敏感,会超过美院教师。这是因为长期训练的结果。画院画家总是阶段性地要为国家的中心工作完成一些命题创作,参与大大小小的“美术工程”,领受一些创作任务,久而久之,会形成某些艺术思维定势,自觉或不自觉,会站在“东家”的立场审视自己的创作,就会塑造出一种有统一审美标准但不一定说得清楚的“国家美学”风范。这种“国家美学”风范,有人激赏,有人厌恶,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体制约束的结果,也是被艺术家塑造和自我塑造互动博弈的结果。
而体制外的自由画家(江湖和市井画家除外),就是为了反抗这种体制化约束而选择了逃逸与放逐。但真正的自由似乎也没有实现。在生存的压力下,许多极有才华的艺术家选择了符号化自我的创作方式,在市场认知的诱导下,走向商业化的自我复制。他们没有就范于“国家美学”,这是一种勇气,但就范于“市场美学”,也不见得就是一条逃往自由之路。
在初步讨论了中国美术生态的“三国演义”后,我们回头再来回答那个问题:为什么选择梁占岩、袁武、张江舟三位画院体制的画家做一次“集结”?为什么要把他们“集结”在美术院校?意义何在?
从军事行动看,集结是为了突击,或者,为了突围。
这三位水墨人物画家,不仅同在画院,而且年龄接近,生长的时代一致,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当过兵,都曾为军旅画家。我们知道,军旅画家是贯彻“国家意志”的一支美术生力军,在他们的作品中,“国家美学”的痕迹最为浓重和强烈。
所谓“国家美学”,具体到中国来说,指的是一种从20世纪50年代逐渐确立起来的美学风格,它在公共建筑(如著名的北京50年代十大建筑)、装饰(如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雕塑(如农业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绘画(如历届全国美展的获奖作品和专为各博物馆创作的历史画)、音乐(如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戏剧(如八大革命样板戏)、电影(如“三大战役”)中均有表现。国家美学的基本要义包括:宏大叙事框架(一般出之以国家、民族、党、人民的名义);典型事件与人物(一般都是领袖、名人、英雄、模范、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新闻);写实手法(一定要具象,可以有夸张变形,但须有度);崇高风格(吸收古典主义的庄重、浪漫主义的激情,但必须积极乐观向上);民族特色(借鉴中国传统艺术的语言风格与表达手段);时代精神(一看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气象)。当然,也适当允许在“国家美学”大框架缝隙中的“小清新”、“小抒情”、“小闲适”,但只是补充,不能冲击“国家美学”的黄钟大吕。
如果从美术史的纵横维度来看,这种“国家美学”其实是中外古典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集合和翻版,与同时期盛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完全错位。在西方已经式微甚至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的写实主义具象艺术,在中国却由于“国家”的扶助和强制推行,在与现实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博弈中,逐渐取得正统地位,成为“国家美学”的要义之一,体制化的专业美术教育,就教这个,就培养美术人群(不管是创作者还是观赏者)对写实具象艺术的思维与审美习惯,内化为民众的艺术素养。
西方式的写实具象艺术,如果从郎士宁来到清朝宫廷算起,它到达中土并以之描绘中华物象,影响中国人观物取象的视思维和传移模写的手法,已经有300年了。刚开始,它被当作一种视觉魔术,新奇好玩,但与性灵无关,与笔墨无涉,与意象殊绝,故士大夫只是把它看作各种“奇技淫巧”之一,没把它放在眼里。但帝王不这么看,从宫廷所传郎士宁等欧洲传教士画家作画之多,题材分布之广,可以看出,清朝皇帝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来自西洋的写实具象绘画,对于表现中国士大夫的“内圣”虽然无能为力,但对于记录和传播中国帝王的“外王”功业,却非常胜任,岂止胜任,简直超迈乎中国绘画之上!所以,是清朝的皇帝,主要是雍正和乾隆,为西洋写实具象艺术在中国宫廷,找到了第一个落脚点。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对接,一上来就是描绘宫廷、帝王、圣业、丰功、祥瑞、苑囿、宝马、香草这一系列符合“国家美学”的东西(黄宾虹称之为“君学”),说明它在被士大夫婉拒的同时,却受到了帝王的特殊青睐。如果我们现在要举办一个康雍乾盛世的展览,撑场子的,还只有郎士宁的画。
这是西方写实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的序曲。接下来,就是19世纪在广州、上海等开埠城市,市民对写实具象绘画的热烈追逐。这种来自社会下层的“美术新潮”,有很浓的殖民地文化心态,是一种“时尚”文化,没有太深的文化思想意蕴。但是有一条,它反映出西方写实具象绘画的世俗性在中国已经获得民众欢迎。因为它特别符合人类的视觉常识,比之中国以线造型并强调线的概括性和书写性的绘画,自然更通俗直观,所以更受普罗大众欢迎。这会形成一股力量,在中国美术史上,这种世俗性本来没有太大的力量和话语权,但在接下来的时代巨变中,当帝国变为民国,民众的话语权增大,在美术上,要求通俗直观,符合视觉常识,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从社会接受的一方倒逼创作的一方。而中国的社会革命,从总体上推动了文化革命和美术革命。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与接踵而至的国民革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发动民众,觉悟民众,激发民众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让他们获得参与感。因此,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精英们就会要求美术精英们适应这种时代巨变。于是,中国的美术精英们就成为夹在新的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中的“馅儿”。美术界的分裂和分野立马显现,旧的美术精英无法适应,开始以“国粹”之名发起文化抵抗;而新的美术精英干脆出洋深造,去欧洲学习,有人自诩为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有人诗意地说是到欧罗巴去借一支芦笛。
但是,20世纪初的欧洲,也正在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来自中国的美术青年,只能凭运气和个人兴趣,或者进入古典绘画的课堂,或者闯进现代艺术的沙龙。他们用“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既拿回来了古典的写实主义,也拿回来了时兴的现代主义。对于蔡元培这位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设计师来说,这都是他实施“以美育代宗教”从而改造国民性的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本无分彼此和高下,更遑论落后与先进。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美术发展中,写实主义的“盗火者”却逐渐居于道德的高地,并同政治精英合流,主动地以其世俗性和“科学性”参与到国民启蒙甚至救亡图存的社会革命的洪流之中,从而以排他性的政治优势取得了新中国美术的正统地位。而现代主义的“借芦笛”者,却因为其不通俗、太自我,而在中国革命中失去其民众基础,从而被边缘化,只能成为一种现代的新式的“文人画”,野逸孤独于主流美术和大众美术之外。从其代表人物的个人命运,就可以看出这一历史的选择。徐悲鸿、蒋兆和、吴作人,同林风眠、李金发、吴大羽相比,前三人“居庙堂之高”,后三人“处江湖之远”,在新中国美术的实际存在中,真有霄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