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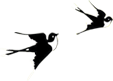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焦点新闻
当前位置:首页 -- 焦点新闻 任颐,字伯年(1840-1896),生于浙江,名雄海上,清末时期画坛独树一帜。他的绘画作品不仅打破了前清沉沉欲眠的态势,更是影响了二十世纪整个画坛的承接和发展。
《驴背吟梅图》立轴,为纸本设色,纵176,横96cm,作于光绪丙戌春(1886年)正月上旬。这幅作品并非他的代表之作,作品打动人的关键,首先是感情的流露。当笔情、墨情、与真情聚积在一起时,无意地释放出了自身的天分,一幅上等作品的诞生应为情与才的显现,《驴背吟梅图》正因如此。

图中两人一驴,寒冬季节。一位彬彬老者,不顾霜天冰冻,一顶斗笠,项上围巾只留出神情自若的面部五官,风衣把人裹为一个整体出色的造型正坐于驴背之上。与旁边一位书僮,同往深山疏林处,寻得傲骨铮铮的腊梅为友,话与短长,只为心诗欲流。看那面部表情的充融,荡涤着一腔切切情愫,欲将诗性彻底而奔发的兴奋。室外赏梅自然一番神情如酥,腊冬的山色谦溢严和,之下的疏散梅林带着清野的奇香,沁心醉人、勾人诗怀。那天色近晚,全无归心,实在难以相别,无奈之余折得一组梅技,念念有词地由僮仆肩扛而返,乐意融融,读者自然与之相应其中。

《驴背吟梅图》画面形式的第一感觉被情而牵。它的用笔表达常有平淡中悠藏声节,画面能简则简、有则必须,构图自然而精妙,形式结合想象空间皆得益彰。任伯年的绘画作品虽然多以穷款,就他行笔流畅中的微妙转折、变迁足以吸引人的审美感观。他又多以中国绘画传统中十八描之“丁头鼠尾”为绘基,加之他俱生以来的绘画天分,把每一根“线”条用得合情合理,在阴阳顿挫之间张扬出韵律的舒情与线条变化后的雄浑,使造形更为精彩,真是美得让人不知所以然了。于情于理、于笔于墨可算是没有一点点刻意之处,书僮肩上的一枝腊梅,参差成音的枝条繁而有势,正好打破了两人一驴三者之间的同等块面。

再看,斗笠的顶部白霜似雪,竹片斜着交叉穿插成的边沿,确成一个灰度,淡淡的赭石敷在面部,确好一条黑色围巾与书僮的帽子和驴同色,三者之间的互应又正好把三者的不同层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任伯年的勾线犹如弄琴般的生动,丰富的变化蕴藏着艺术最真切地的情感,总能诉说到读者对他作品审美的高度,渗透到骨子里面的愉悦,会意而静心地畅游于画面疏密技法的享受,品评着情感驾驭笔墨表达的丝丝内涵,诉颂在一帧画面的天地之间。可见一幅好的作品,魅力无穷,以情达意何等之重要。
/家训丁酉寒冬於敬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