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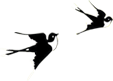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论坛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论坛 书画艺术只要一谈到物质性,层次上似乎就差些,总是没有谈论精神性来得高尚。相较精神层面,物质性的东西感觉就是比较枝微末节,离风格表现距离较远,而且难登大雅之堂。时至今日,多数的书画史研究文章都很少会谈论到物质的部份,这些对于物质缺乏关怀的文章中都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古今书画家皆使用相同的笔、墨、纸、砚。只要稍有画画写字经验的人,都可以轻易地质疑这个已经成为书画研究「定律」的不成文假设。
尽管物质老是在书画史中缺席?必要的时候却往往扮演关键性角色,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图1)。无论《兰亭序》之真伪,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出此作的书风与王羲之其它作品相当不一样,为了解释风格上的不同,说故事的人将物质给搬了出来,特别指出书家在书写时用了鼠须笔、茧纸这两样特殊物质,深怕无力说服,连天气与酒都来加油添醋,好让大家深信不疑。《兰亭序》的例子确实可以充分说明物质在书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书法、物质与风格三者之间的关系。
物质对于书画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人尽皆知的道理,这个观点正好可以用在书画的研究与鉴定上,从创作工具的物质面来思考书画风格,同时也可以在真伪鉴定上有很大的帮助。以下就举笔者办过的两个展览稍加说明。
沈周
沈周单纯的书法创作不多,大部分被讨论的书法作品都是题在画上的题识或题跋,所以他多数的书法都是写在绘画用纸上(绢的使用较少)。关于沈周的绘画用纸,就传世作品看来,他比较偏好某种加工纸。这类的纸的表面阻力较大,所以快速移动毛笔时线条的轮廓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移动缓慢时又会因为宣纸的吸水性而产生晕开效果,可以制造出丰富的线条质感与多层次的晕染,因此成为明代画家喜爱使用的材质。
对于这种纸张的偏好似乎也影响到沈周的书写用纸,因为他的传世书迹也多半书写在这类的加工纸上。关于这种纸张对于书法线条所产生的效果,线条的两侧因粗涩纸张表面而产生锯齿状的边缘,同时也让墨色的吸收产生变化,造成枯燥浓淡不一的丰富视觉效果,《落花诗图并诗》的诗文部分便是一例(图2)。
目前在沈周的书法研究上,较少学者关心材质的影响。由于沈周一些风格特殊的书法作品,恰好也都是写在性质特殊的纸张上,所以有必要深入探讨材质可能对沈周书法所造成的影响。
沈周六十二岁(1488)题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图3)就是一件相当特别的作品,乍看虽然颇有黄庭坚风格,不过出现不少用笔与书写的失误,全作也使用较多光洁滑顺的用笔,与同时期的颤笔习惯不同,反而接近早年书迹的用笔特征,结字上也掺杂早期端整的风格。事实上,此作光整修洁的线条显示出沈周对这类书写用纸并不熟悉;若再从墨色停留在纸面的拒墨状况看来,这张纸是确实属于比较光滑细密的纸,纸面也可以见到明显的细碎纤维,这些纸质特征与当时很受到苏州书法家所喜爱的藏经纸相符。书史上著名的「吴中三家」(祝允明、文征明与王宠)都是这种光滑藏经纸的爱用者,且留下不少书写在这种纸上的作品传世。相较之下,沈周对这种特殊的纸质特性还是十分生疏,无法如同那些专业书家一样可以自由地将自己独特的风格书写出来。
沈周所发展出来的黄庭坚风格在运笔时,毛笔的确需要较多的摆动动作。对于沈周而言,这些摆动动作在纸面粗涩的加工纸上比较可以挥洒自如,而光滑的纸面显然无法提供颤笔所需的足够摩擦力,因此无论在力道或是掌控上都显得力不从心。显然,材质上的掌控难度迫使沈周采取不同的书写策略,回复到自己最为熟悉的早年用笔,仅在部分笔画与结字上稍事做为,并未见到挥洒自如的书写状态。从纸张材质的角度而言,沈周此跋的特殊性正是因为对于此种材质的掌握度不够所造成,而非出于他人之手。
从传世书迹中可以发现,藏经纸在明中期的苏州地区相当盛行,因此沈周必然有不少机会可以接触到这种纸,也就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熟悉这种材质。事实上,随着年纪的增加,沈周对在这种光滑藏经纸的书写能力确实是有所提升,他七十六岁(1502)跋传王维《江干雪意图》(图4)也是书写在类似的藏经纸上,展现出更加熟练的控笔能力。全作字形维持一贯的细瘦紧结,用笔粗细变化较大,抖动颤笔增加不少,不过还是掺杂不少平直光滑的用笔,整体风格上符合其黄庭坚书风。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不少笔画的起收笔处皆因为纸张摩擦力不足而导致毛笔有稍微失控打滑的状况,例如二、三行的「今」与「寒」的捺笔,就显得用力太过而变形,同样的力度在摩擦力较大的加工纸上很可能就是完美的捺笔。这些因纸张特性所产生的微小失控处让全作的线条看起来尖锐而且毛躁,有些线条还因此而显得单薄,与他寻常作品中的苍劲浑厚相去甚远。
沈周无纪年题唐寅(1470-1524)《对竹图》(图5)则是书写在金粟山藏经纸上,唐寅此画可能成于一四九八年,或许沈周也是题于此际。就书风而言,沈周此题确实与题《富春山居图》的风格比较接近。题《对竹图》也是尽量避免使用黄庭坚笔法的书写状况,结字也比较端正,属于比较传统的风格。此作整体书风虽然比较稳健精谨,不过还是出现了沈周书写藏经纸时的类似问题,部分线条同样略显毛躁与扁薄。显然,沈周在面对无法自由地书写出黄庭坚体的藏经纸时,选择采用他根深蒂固的早年传统书风,只是在笔力上更加挺劲,结体也比较紧结。
这三张书写在藏经纸上的作品是沈周不同年代的题跋,反映出他对于这种纸似乎一直未能驾轻就熟,也指出这肯定不会是沈周心目中理想的书写材质,同时也凸显出题跋书法所可能具有的侷限性。也就是说,沈周在题跋的当下,用来书写的纸张可能已经被限制住,这时无论沈周喜爱与否都只能接受,所以才会书写出这些不尽满意的特殊作品。反观沈周的《落花诗图并诗》,就是使用他所习惯的书写用纸,所以他驾轻就熟、相当自在地书写出很标准的黄庭坚风格行书,完全没有书写在藏经纸上那种不顺手的感觉。
董其昌
董其昌个人的用笔习惯也很值得注意,与其书法表现有密切关系。倪后瞻描述道:
凡有新笔,先以滚水洗毫二、三分,胶腥败,毫为之一净。则刚健者遇滚水必软熟,与笔中柔毫为一类,然后以指攒圆,不可令褊,攒直不可令曲,干三、四日后,剔砚上垢,去墨星,新水浓研,即以前干笔饱蘸,不可濡水,仍深二、三分,随意作大小百余字,再以指攒圆攒直,又听干收贮。临用时,量所用笔头浅深,以清水缓开如意中式,然后蘸墨。此法传自玄宰先生。
开新笔时先以滚水开前面十分之二、三,将毫上的胶、腥味洗去,三、四日后以干笔沾浓墨书写百余字,之后收贮好,待准备书写时再视所需决定开笔的深浅,以清水缓缓泡开毛笔。书写前的开笔详细步骤如下:
凡欲作字先开笔,开笔之法,先点清水,少歇又点,如此两三次,令水透毫,然后取笔向干净砚上旋转轻捺,令四面之毫无一丝不和,又由浅入深,令四面毫之润处无一丝不齐,酌字之大小,以分浅深。若临米,纵写小字亦须深开,方运用轻重如意也。至于研墨、点墨,另有口诀。若写毕,亦有秘传。此学书第一要法也。
先以清水分三次慢慢将笔毫浸润泡开,利用干净砚面整理笔毫,使其毫毛整齐和顺,至于决定笔毫发开的多寡则是「酌字大小,以分浅深」。董其昌显然使用较大的毛笔,依字体大小决定开笔之比例,而非完全发开,如此的蓄墨量必然受到很大的限制。
董其昌未将笔毫完全发开的用笔方式,从其行草作品中粗细变化不大的线条也可以察觉到,草书作品中更加明显。此外,董其昌也经常将笔毫压到底来书写,飞白线条中可以见到笔毫底部用力刮过纸面的线条(图6),枯笔的转折则是容易出现许多叉出毫毛所造成的不干净笔画(图7)。事实上,在笔毫完全发开的状况下,很少书家会将笔毫压到底书写,因为所有笔毛都会随意岔开而无法控制。董其昌将毛笔压到底还能书写,表示这只笔毫根本没有全部发开,才能如此书写。至于董其昌使用完全发开毛笔的例子,可以参考〈论书〉(图8)册,他特别提到是羊毛画笔,而一般画笔都是完全发开,所以不仅蓄墨量丰富,线条粗细变化也比较悬殊,柔软的笔毫也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趣味。
传世董其昌书迹的线条在秀润之外尚带有挺劲度,此种质感有赖于较佳的笔毫弹性,柔软的毫料是难以达到。为了在柔软的毫料上获得这种性能,其长锋毛笔便不能全部发开,仅能使用毛笔前端来书写。这种只开前端的毛笔不仅书写起来健劲许多,未发开的坚硬部分也有助于将运笔的动作力量精确地传达到笔端,可以清楚地将书写动作展示于纸面上。至于完全发开的软毫,柔弱的特性很容易将来自手部的运笔力量吸收掉,笔毫在控制与反应上也慢上许多。软毫笔书写的线条虽然看起来比较丰厚,但是往往因反应迟钝而变得模糊不精致。为了书写出精致而秀润的线条,董其昌显然针对软毫在控笔上的不足,采取了部分开笔的方式来加以改善。
尽管毛笔未完全发开的方式可以获得书写所需的弹性,却也意味着蓄墨量的严重不足,这对于书写连贯性强的行草当然是个大问题,屡屡沾墨不仅影响书写节奏与流畅度,也容易导致行气的衔接不顺。从蓄墨不足的角度来思考董其昌最喜爱的高丽纸、宣德笺、藏经纸与撒金笺,可以发现它们表面光滑细腻与不易晕开的特质正是关键。面对笔毫弹性与蓄墨量的两难,董其昌智慧地将目光转向纸张材质上,也确实让他找到能够大量节省墨汁的纸张,顺利地解决蓄墨量不足的问题。由于只发开前端的毛笔蓄墨量真的很少,即使找到省墨的纸,字只要稍大些,还是很容易就出现枯笔飞白的效果,这也成为其书法的一项特色。
显然,沈周或是董其昌的书法中都有因物质而产生的特殊现象,这些部份无论是从书家的艺术理论或是创作力都很难加以理解,因此不得不从物质层面加以考虑。中国书画的物质性虽然长久以来在研究论述中被忽略,不过这些物质的影响力却从未消失过,只是被混杂于创作者的艺术风格中,等待我们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