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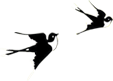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论坛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论坛 明人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提出了南北宗之说,将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驌,以至马、夏辈定为北宗。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法,其传为张躁、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称为南宗。
董氏论述南北宗之说亦是后来演为文人绘画与匠画之别,水墨与色设之分,其弊尤甚。自魏晋以来,绘事一科表现方法不同而操笔者皆为读书之人。故不能以文人画而分论之,当以风格面貌论亦不可有短长褒微之词,南北画宗交相辉映,成就画史,其内容丰富矣。魏晋顾、陆、张、宗炳、王微等诸家,皆风流之文客,于书画之外著宏文冠绝天下。展子虔、阎立本、吴道玄、张操、王罔川、李思训父子皆学养涵盖宽博,亦善艺理,学贯古今。董源、荆浩、关仝、郭熙、李唐、米襄阳、李伯时、文与可、苏子瞻及南宋诸人堪称胸藏锦绣,腹为诗书,千载隆誉。元季赵子昂、钱瞬举、高克恭及子久、吴镇、元林、王蒙更有明代吴门诸客,莫不以文滋养画境,笔墨得于此而图画永恒。
故自古画者皆属文人,只不过随时代之变革,生活方式及审美情趣之演变,艺术创作也随之变矣。人物由魏晋清逸之内相接近生活化为唐妆,山水由技简而繁密,水墨金碧造一时之大观。五代宋初巅峰绝叹,廟堂气象于天下统一无不相关,宋人全景之作将山水真境推向极致,意足笔备,墨韵华章,烟雨云湿,潇湘奇景。人物上承魏晋参道子玄妙,逸格于梁楷而花卉徐黄两体各擅经营,传法酻而定繁花锦蕾,疏密有致。一时画道之盛而内涵丰富于心境文思之变而互为养之,使绘者思于内溢于外,文心诗境尽现,绘事完备矣。北宋绘画之发展,不得不谈受欧阳修古文运动及宋代理学的影响,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力追韩愈又与之不同,雍容、平易,意境深远,以平实代险怪,于跌宕气味代词藻。这是欧阳修古文运动与思想境界的追求,其艺术性格当属于山水画中的平远。而唐宋八家中的王安石文章诗境,是高远与深远的相合。曾巩平远中略含深远,苏轼、苏辙集平远、深远、高远三者相融而形成的文学艺术精神及生命性格,是苏轼绘画思想的全部内涵。黄鲁直深远归于平远,古淡天真,反映出其文学与艺术的心源。北宋文人在继承前人诗文回归相通处冥合山水绘画精神,使之在品鉴书画过程中多有独思,获益真谛。以诗文修养衡定画家技道之作,由理论而实践,开辟了时代风气。如苏轼、米芾诸人以诗境幻化境,形成了文人绘画新的流派,其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理论体系完备,为元代绘画奠定了巅峰之基础。然而宋代绘画在继承五代的基础上随着国家的统一,古文运动及理学思潮的影响,山水花鸟创作呈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为后世所不能企极。北宋理学家所讨论的内容是义理、性命之学,是融佛、儒、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石介、胡瑗、孙复被誉为理学三先生,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诸人。则是实际北宋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为宋代理学开山之祖,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体系。邵雍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并使之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张载则发展了气一元论思想,为古代中国辩证法两一学说的集成者。二程兄弟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他们为北宋的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以理为万事万物之本源,亦为天理,承认事物的变化。认为理有神秘力量,阐述了天人关系,天人相与的命题。在认识论上比较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讲求穷理。其核心范畴是理学中的本原论“理”、“气”与功夫论的“涵养”,北宋文人将这些理学内涵渗透在画论之中,形成了绘画理论中“画理”、“画气”及对画家人格修养的要求。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影响着北宋的绘画观念。于载道抒情,静观取景,身即山川而取之的艺术构思及表达方式构成了一个时代创作思维观,从而完成了北宋绘画笔墨设色构图题材意境审美追求的境界,呈现出北宋绘画的时代风格与整体面貌。这种面貌是理学观物内省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旨趣以及天人合一思想的结果。北宋绘画受理学影响,在取材、立意、构图、样式及创作实践中臻于完美,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伦理观念,丰富了作品的人文精神与笔墨内涵。
一个画派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是先以理论奠定其基础,而后以笔墨实践创造其独有的大的流派面貌,使一时之众的风格在丰富中见其个人心性所溢出的自然山川景象,诗词画境。北宋时代的文人对绘画在内容与形式上的要求超越了前人的笔墨与思考,更多的融入人文情怀以文人特有的审美情趣来表现自己对山川万物的认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人画理论体系。
文人画思想的出现与始肇者,当推苏轼为代表。苏氏在《四菩萨阁记》中谓:“始吾先君(苏洵)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尝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苏洵在《嘉祐集》卷十四《吴道子画五星赞》中论,“唯是五星,笔势莫高”。苏老泉对画的雅好可能与唐中叶皇室壁难入蜀留下大批画迹有关。苏轼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然得到无限的熏陶,加之与大画家文同亲戚,与李伯时、王诜、米芾为友,与郭熙、李迪同时相接。因此他对绘画的认识与理解,必然有独到之处,故自许能画、知画。在《石氏画苑记》中云:“余亦善画古木从竹”,这是苏氏对自己能画的告白。朱元晦在《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跋“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此跋正说明苏轼自负决非轻浮醉语。在次韵《李端叔谢送牛戬鸳鸯竹石图》䟦:“知君论将口,似余识画眼”的诗句中,是知画的自许。对画及诗的关点,《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技》二首中尤为见性,“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对后世的文人影响甚大,亦误解甚大。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 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这段论述苏轼以讨论画的原理,认为人类、家禽、宫殿、居室、器物等均有所处之形态。山川、岩石、竹子、柴木,流水、海波、烟雾、云朵,是常幻灭其形态的,但本质存在。当出现形态差异时,人尽可知。事物本质的不同,即便是知画之人也难解其理。所以凡欺世之人获取名声者,一定是依靠事物所不常处之形态来完成。所以,形态的遗漏,必止于表面的遗漏,无常规画出来的画作其形态必然是没有常规的,这是本质上不能严谨所造成的问题。世上画工,作品形态千变万化,其画本质,除了智慧才华之人,他人是无法分辨的。文同所画的青竹、岩石、荒枯之木,可以说是掌握了事物的本质。于生动中表现、枯寂、弯曲、紧缩、畅达,枝根、细茎、枝节、叶片,纹路、凸起,千变万化,似乎不循规律,然又何乎天地所生,满足了人的意愿。为明智达理之士所喜爱!
苏轼《墨君堂记》中载“...........然与可独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矣”。此段论述了文同画竹得其情而尽其性,身与化竹,成竹在胸的境界。这一境界是通过得其常理精神超越,忘去世俗,持以虚静竹入其心,主客一体互为拟化而获,即《庄子.齐物论》中所谓的“物化”。
东坡《书晁䃼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诗中有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苏轼从庄周物化的意境中,得出画的奥妙,直探艺术精神之本源。身以物化,这是艺术家的关建所在。《宣和要谱》卷七李伯时条下记“公麟初喜画马,大率学韩干,略有增损,有道人教以不可习,恐流入马趣;公麟悟其旨,更为佛道,尤佳”。画马须得马趣,身不能与马化亦难画之。又说公麟能画山水,“皆其胸中所蕴”。故画山水之人,胸中必有丘壑。然胸中丘壑又不可为主观之主体,当在虚静中藏。苏氏跋《加王定国所藏王诜画著色山》二首其一谓:“........烦君纸上影,照我心中山。........我心空无物,斯文何足关。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亦是此理,身化物态,物融自己精神之内又原于生活超越世俗的作品,才是通往殿堂的艺术。苏轼《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诗》,尽诉其创作经历。“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苏氏认为艺术创作,有时是离不开酒的,酒能使人从尘俗中得到暂时的超脱,进入美的意识,在超脱状态下完成并显现出作品美的内涵与真境,酒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作用。
黄鲁直《苏李画枯木道士赋》中谓:“滑稽于秋兔之毫,尤以酒而能神”。《题子瞻画竹石诗》“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说明了酒与诗画的不解之缘,弥久而不可分离。周必大《题张光宇所藏东坡画》云:“英气自然,乃可贵重。五日一石,岂知此耶”。周氏论述正是苏氏在记文同画竹《篔簹谷偃竹记》过程中的阐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苏轼认为“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竹子的生命是一个整体,把握竹子的整体亦是把握了竹子的生命,竹子的生命握不是对竹子的认识而对竹子精神的理解与整体性的观照。将观照内藏成相而忘象进入精神自由的创作之中,“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此状态亦是庄子所谓的“运近成风”“解衣磅薄”,是对一个伟大艺术家创作情形的描述。
苏氏在《书蒲永升画后》中说“始知微(孙)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卒入寺,索笔切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奔屋也”。这正恰与庄子合,又《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有“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之句。亦是“诗画本一律”的左证。画竹忘竹,由巧忘巧,心手相应是庄子对技进乎于道的要求,苏轼《众妙堂记》中对技与学有着深刻的描述。“子亦见夫蜩与鸡乎?蜩登木而号,不知止也。鸡俯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其蜕与伏也,则无视无听,无饥无渴,默化于慌惚之中,而候伺于毫发之间,虽圣智不及也。是岂技与习之助乎”。此一则论述技巧学而忘乎其技与习,正是《庄子.养生主》技进乎于道的比拟。由此知庄学对苏氏的潜移默化。滋养其心性中的萧疏雅淡,枯木竹石的性格,及审美的归宿。
以禅论画之始,当推黄鲁直,但又非以禅直入画境者。
黄氏虽然在《题赵公佑画》中云:“余未尝识画。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观图画悉知其巧拙功楛,造微入妙。然此岂可有单见寡闻者道哉”。黄山谷在参禅识画中,实际上是以禅悟通达庄学之境,由庄学而知画,非以禅识画。庄子要求“无用之用”,无知无欲,禅亦要求解粘去缚,“无功之功”,庄子以镜喻心,禅亦以镜反观,二者相同。然而又互不影响㝠符巧合。
庄学与禅宗有同处亦终归于异。庄学要求由无知无欲达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使人生更有意议,更为喜悦,从尘俗中解脱,不否定生命的意义,不要求从生命中解脱。禅宗的根本核心是以人生为苦谛,否定生命,从生命中解脱。庄子对人生的纠葛要求在“坐忘”中得到“化解”,认为宇宙的生命是变化的,人通过“物化”将宇宙万物加以拟人化,情感化。使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官天地,府万物”。“能胜物而不伤”。在虚静心中有“丘壑”。禅宗对人生的俗葛则要求的是“寂灭”,四大皆空,“本来无一物”的人与物之间是无的关系。所以禅以无念为宗,不求形质,不聚丘壑,无知于画,不成于图。故蒼雪大师有“问子画得虚空否”句?虚空否?亦无画。唐代是禅宗鼎盛时期,但唐代人尚未以禅论画,到是宋时文人多有淸谈,似乎以禅论画,但实际则是禅表庄内。黄山谷喜禅悦,论画则是庄子意境,而非禅境。
节选于张继刚先生《砚池滴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