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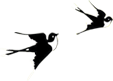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霍春阳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霍春阳 > 艺术作品 时间:2017-03-22 04:29:30
30年前,雨狂风骤的十年“文革”结束,天津一副描绘迎春花绽放的作品,成功地表现了人们的心花怒放和无限生机,在全国美展中赢得普遍美誉。两名作者都是天津人,其一是画界耳熟能详的孙其峰,另一便是开始崭露头角的霍春阳,霍春阳是孙其峰的学生,那时只有30岁。此后,随着他不断推出新作,不断悟入艺术的真谛,不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在艺术思想回归深层传统后,渐渐形成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格。十余年来,这种风格日益完善,不胫而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中国画坛上,霍春阳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中年实力派画家,虽然实力派画家也不下数十人,但有的实力在造型,另些实力在笔墨,而霍春阳的实力是全方位的,尤以讲求境界的小写意花鸟为胜。
“文革”后的小写意花鸟,有两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一是改变了传统的折枝布局,画林间花草的原生态,层次丰富,茂密繁盛。二是改变传统的水墨为尚,推进晚清近代以来对色彩的发挥,追求不同于前人的视觉效果,而霍春阳的小写意花鸟,却以简静的特色卓然而立,不但形简神完,笔精墨妙,尤擅淡墨干笔,而且简约疏淡,或疏花简叶,或只鸟片石,空灵虚静,优秀淡远。一切历历如在目前生动形象,都无例外地隐约在光风?月之中,清如水洗,静如天籁,似有若无,欲显还隐,真可谓“若恍若惚,其中有象”。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目中花鸟生命和宇宙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他不满足于讴歌鸟鸣花放的生韵,而是积极引导观者去品味淡而有味的太羹玄酒,去感悟充满光明与智慧的精神之光,特别致力于作品精神境界的玄远灵明。这真是霍春阳的独到之处,也是相当一部分画家忽略的。
如今,随着城市话的迅猛进程,流行文化的追波逐浪,许多画家为了引人注目,每每着意开发眼球效应,笃力追求视觉冲击,尚繁复铺陈,讲平面构成,崇色彩缤纷,甚至以刻画为工,以躁动为美,为此而花费心思引进西方的观念,在不同程度上梳离了传统的奥义。对于前人所讲的“赏心悦目”四字,得其悦目而失其赏心。霍春阳作为具有独特代表性的小写意花鸟画家,他的艺术不仅好在赏心而且贵在养心,实际上,多年来他的艺术探索一直围绕着在花鸟里表现前人很少致力的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方面就是超越自我与大化同一的超逸精神。所以我说,霍春阳是当代少见的逸品画家。
中国的艺术精神,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群体的执著精神,或以艺“载道”,着重反映并介入生活,“成教化,助人伦”,发挥其教育认识职能;或颂品节情操,讴歌心灵的升华,影响受众的精神品格。旨在避免内忧外患造成的基本价值观的失落,促成社会进步以及和谐安定的发展,过去称之为神品,另一个是个体的超逸精神,旨在面对困境与异化的现实,发挥其畅神——也就是精神逍遥的职能,艺术地营造一种摆脱异化、远离困扰,进入天人合一的宇宙诗境。旨在表现一种被过滤了的现实,一种活泼泼的生命意识,一种升华了的精神境界。过去称之为逸品。
自古以来,人物画更多承担了第一种职能,文人山水花鸟画更多呈现了第二种职能。然而,霍春阳的花鸟逸品,却把个体的畅神与净化升华群体的神境界结合起来,他的花鸟画,题材是古已有之,“四君子”占了很大的比重。造型属于“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一般画鸟形似的成分多一些,画花木形似的成分少一些,非常适合早已自觉不自觉接受了传统既成图式的中国观众。笔墨严格恪守前人规范,但运用得生动自由从容不迫。他的每张画都不画太多的东西,都以水墨为主不用浓重火爆的色彩,偶尔利用灰黄的纸色,恰当地点染百粉,画里疏淡和悦的花鸟彷佛融进了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呈现出虚静空明的灵光。
自古以来,画中逸品的阐述者,都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的超越,二是笔墨表现的简约,三是境界的深静。对此,清代的恽寿平指出:“逸品其意难言之矣,饴如卢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风也。”“画以简约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烟鬓翠黛,敛容而退矣。”“造化之理,至静至深。”前辈美学家宗白华,更把深静看作中国艺术表现文化的精神,他指出:“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静寂。”霍春阳的艺术恰恰具有上述的三个特点,可谓默契造化,简约深静,“幽情秀骨,思在天地”。
正如前贤所述,在传统哲学思想的陶融下,中国艺术虽然无例外地作用于感官,但从不满足于感官的刺激,而是千方百计地引导观者超越感官,在体味“内美”或称“隐秀”中,进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而只有深沉静默之境,才足以使内在的精神活动,在物我两忘中,达到一种超越艺术语言和物质世界的自由安详。对此深有体会的霍春阳,他的艺术正是有意疏离刺激人眼球的色线形,在表现对花鸟情境的微妙感动的同时,努力把欣赏者的神思引向悠远无际的大化。他的画里着重表现的是一种“象外意”,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群体精神,是在更高的没有烦扰、没有困惑、没有利害的宇宙诗境中获得的灵魂净化和精神自由。
霍春阳的艺术,从描写灿烂绽放迎春花的《山花烂漫》的有我之境,走到如今的无我之境,关键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大变。在80年代中后期,他像许多画家一样地向往新变,曾取法明清个性派的大写意,表现旺盛的激情,张扬创作的个性;也曾学习黄永玉富于构成意味的荷花,还曾把西方的构成手段,石涛式的山水和日本的少数字结合起来,追新逐异,务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但自从他探索新文人画以来,便开始追究中国画艺术精神与传统哲学思想的关系,抓住了在传统文人画里表现得比较充分的以畅神为依归、以净化心灵和提升精神境界为目标的努力方向,为此挖掘传统,发扬光大,没有只在笔墨上、图式上、肌理上、表现主义式的感情发泄上下表面工夫,既排斥了盲目西化的干扰,又从深层挖掘并激活着传统,我看这是一种由技进道的追求,是他比一般浅学画家高明的地方。
当代的中年画家,包括霍春阳在内,大多出身于美术院校,所有的美学院校又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虽然学的是国画,但殊少国学基础,思维方式与创作方法也接近西方的艺术家,常常把创新与传统对立起来,对于传统是传承明清个性派多,对上溯宋元的所谓正统派弃如敝幄。霍春阳的变法由个性派泼辣枞横的大写转入超越个性派境界空明的小写,首先得益于对传统文人画的潜入,新文人画作为西潮澎湃中的对立物,比较重视衔接近代几乎断裂的传统底蕴,讲老庄与禅学与艺术创作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为多。大约在参与新文人画运动的过程中,他理解了老庄和禅学的超越精神,当时写给我一幅书法,写的就是“禅意”二字。
然而进一步领会传统艺术文化的博大情深,则得益于随后而来的国学补课,他主动参加了北大汤一介主持的“中西文化比较学习班”,以及其后的“中西文化比较高级研究班”。在班上,他首次接触了国内一流学者,了解了梁漱溟等新儒学大家思想,甚至买来梁氏的《人心和人生》《中国文化要义》,反复研读,同时他又拜访了吴玉如,吴玉如说传统中《文心雕龙》还属于词章,《论语》《孟子》才是经典。其后他牢记吴氏的一席话,用很多时间去研究儒家经典,并且在领会中国的文化思想中打通儒道禅。古人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以为逸品,超逸精神渊源于个人解脱的庄禅,但霍春阳的逸品画与某些古代画家的高涛远引的出世志趣不同,他是以貌似出世的超越,做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入世事业,是在异化的威胁中重建着充满自信的精神家园。
当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文明的飞速进步,商品价值的极端追求,功利效用的精打细算,快餐文化的流行,人与自然的疏离,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不少人内心世界的浅薄、空虚、苦闷,无助和精神家园的失落,强势群体未必强在文化,随着钱权的增多,压力也与日俱增。弱势群体缺乏支配力量,尤觉困惑烦恼,除去政府政策对科技与文化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宏观调控外,发挥艺术精神的两个方面的互补作用,也成为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需要。对于花鸟画家而言,发扬表现超越精神的传统,以升华国家的精神品格为前提,以艺术地营造有高品位精神境界的作品为归依,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人们的精神,使国人的价值观、创造与精神自由在艺术中得以实现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我见过一副对子,写的是“立脚不随流俗转,宅心能到古人难”。霍先生正是一个不随流俗守护传统的画家,他在倡导逸品画的创作与教学中,提出了若干振聋发聩的见解,比如他引用禅学著作《青言集》“无异言而生清净心”的主张。指出不应该把花样翻新与否视为衡量绘画优劣的标准。他还指出,“有风格并不代表有质量”,“艺术应该淡化个性,把艺术的共性容纳得越多,艺术的个性才越有价值”。他的这些与时下话语很不相同的看法,尽管未必获得致思周密的理论家的完全同意,但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以来艺术认识上的一些迷误。
站在20世纪里边看20世纪,就像在庐山里看庐山一样,不容易看清楚。只有把20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放在世界范围的历史长河里去看,才会发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一直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之下,一直在科学主义的批判之下,中国画也一直在西方标准和科学而非文化的标准的改造之下。霍先生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在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智者。尽管对绘画与现实关系的执著与超越、对传统的因与革、对艺术的个性与共性、对绘画的视觉特点与文化内涵的关系,还可以深入讨论,从理论上阐述得更有分寸,但霍先生的看法是切中时弊的,是抓了要害的。他致力于提高精神境界的逸品画,无疑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他正在思想艺术成熟的壮年,我相信他会围绕这弘扬传统给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他已经着手上路了,任重道远,我和大家都期望他的潜力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为21世纪中国艺术的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现以《观霍春阳画》小诗一首结束这篇短文:
疏花淡叶泛青光,虚静空明意味长。观化观生神自逸,津门常忆霍春阳。
薛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