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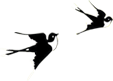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霍春阳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霍春阳 > 艺术作品 时间:2017-03-22 04:27:00
考察霍春阳先生的绘画艺术,我们不得不先从传统文人画的发展及其特征入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霍春阳先生曾被列入新文人画代表画家的行列,但并没有得到画家本人的认可。因为,在当时的新文人画的思潮中,其艺术主张存在着很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可以说,新文人画的论点是难以成立的。霍先生曾说,“文人画哪还有新旧之分?如果视旧为没有生命的死的东西,那我们至今还学什么元四家、四王四僧呢?!”他主张只有老老实实地画传统,才能从学古人中著己之地。纵观霍春阳先生的作品,早期用笔以书趣风神胜,中期似以飘逸恣肆胜,而现在则已愈发趋向理法和意境,虽大有随心所欲不愈距之意,但始终与传统文人画一脉相承,其间流露的并不是老的旧的东西,相反,一般时代气息夹带着浓浓的书卷气扑鼻而来,这些无不显现着画家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哲学、笔墨和情感内涵的深深了悟。
“彼此不觉之谓神”
“文人画”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宋以后几乎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在其后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的哲学内涵,在因为承认了“道”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性、承认了“心”的物质因素和其可调节性、承认了“性”与“天”的统一性以及在文化上体现的完美性而日趋丰富。明董其昌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说明绘画一旦掌握了天地大理,便掌握了创作的自由!于是“应目会心”和“澄怀观道”成为了绘画创作的重要方法论;清代的石涛也将“一画”作为“万象”的最根本法则,主倡对万事万物“深入其理,曲尽其态”,以求达到“画可从心”的自由创作境界。所以从哲学的角度,中国文人画的最根本的内涵应是以庄子的“自由”思想和由此而展开的审美关系。
霍春阳先生对此三昧独有体悟,他说:“中国画讲究通过物态形象、笔墨境界表达主体对形而上的宇宙之道、人生之道的认识和体验。”他认为,自由的创作源于“心”中要有一个“境界”,即一个人的精神所达到的万物归以的“无我”之境。这种境界是永恒的,是老子的“得道”,是庄子“心斋”、“坐忘”。观霍先生的作品,于许多微妙处洋溢着他的“心斋”,这种空虚的心境,穿行在他笔下苦心经营的百卉灵禽间。正所谓“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只有“虚”,才能实现对“道”的关照,才能“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霍先生的“听之以气”,即以气运画面的构图,以及枝叶的穿插向背,从而获得老庄的自由境界。所有他的画尚简以求不俗,“画以简贵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沉渣,独存孤迥。”孤迥为何?又是“心斋”也。他以“抱一而为天下式”的心态应对目中之物,心中之物。他的“观”很特别:“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心深微而无所见,故能照自然之性。”“观”的一切准则都是为了通过最自然的方式达到最必然结果,即“无我”之境,或称为“神”。对于“神”,古往今来皆用于品评,而霍老师却用于经营。他说:“彼此不觉之谓神”。“觉”,大概可以解释为察觉、觉悟,是用心感悟的意思。但是,用心感悟之心是变化无穷的,对画面对象要做到“彼此不觉”,这是一种何等的秩序啊,这可能就是霍先生追求的“道”吧。
“瘦劲方通神”
在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和代表作品都出自文人画家之手,而非纯粹的职业画家。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文人创造和掌握了文化,它使得绘画的高度能与文化发展的高度相并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媒体——书法。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传承方式都离不开文字,汉文字的文化含量几乎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在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法艺术,更使得汉文字成为具有无限抽象又具有无限内涵的形式载体。文人掌握了汉字,便使得汉字与文化、汉字与书法、书法与线、线与用笔、用笔与绘画形成了艺术与文化的完美结合。于是乎,绘画艺术在文人的手中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创作高峰。线,也就是文人画家宣泄情感,塑造形象,舞文弄墨的主旋律。
霍先生的绘画相当程度地继承了“线语言”的造型原则和表达方式,紧紧抓住“笔墨”这一语言体系,从文化的角度,深入到笔墨的内部,用笔墨传达画家本人对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霍春阳先生在总结用笔时说:“在绘画中的骨法用笔关乎画家的表达能力,也能传达情性。线条中的轻重缓急的变化,更能呈现出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乃至学识修养。”所以他在用笔的变化时,更着重于画面上的物像与线的关系。他画兰花,常常与石头合在一起,用石头磊落、苍劲、灵透的特征衬托出兰花的纤弱、舒展和摇曳,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兰花的性格;他画兰花,方圆左右,纵横上下,虽寥寥几笔,但阴阳刚柔俱应,尤其在兰叶的穿插上,用笔若断若连,意到笔不到,似缓似急,有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于线条的轻重变化中,传达着他的思想和学养。
在霍春阳先生的笔墨语言中,笔和墨是交相呼应的。他似不赞成“大泼彩”和“大泼墨”,认为笔墨是不应该分家的。霍先生之用笔,于素尺方寸间蕴达着力度,这样墨不离笔,看得出是为画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功力所控制的,正所谓“瘦劲方通神”,有力度方可笔下出神而达韵。
而于用“墨”,霍春阳先生说,墨法就是水法。要凭感觉,靠经验。他提出了用墨要有体积和厚度的概念。他在用墨的时候,不是常人用的平涂和拉的方法,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了“揉墨法”。他所说的“墨要有体积和厚度的概念”,就是在“揉墨”中体现的。通过“揉”在毛笔与宣纸的层层叠加中,墨的层次和变化尽显其中。当年黄宾虹前辈总结的用墨七法,把积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使得其作品墨华飞动,浑厚华滋,在厚厚的积墨里呈现出了“亮墨”。霍春阳先生的揉墨法也是自有心得,把用线叠加变为以墨反复与纸揉磨,他画的梅干,就是通过渴笔和渴墨,把行笔的力度和速度控制得恰到好处。把用笔与用墨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墨代色,正是“墨不碍色,色不碍墨。”对墨的把握,使得霍春阳先生的作品单纯、简约,达到了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这样“意足不求颜色似”,亦是画者本色也。在霍春阳的画中,我们找不到古人摒弃的那些浮、软、没有骨气、没有神韵的“浮笔涨墨。”每一点墨到纸上都似是游动的、透气的,干而不燥,湿而不泡,轻松但不轻飘,灵动而暗沉内力,笔轻意重,有光彩,有活力。
“无异言而生清净心”
“情感”是文人画的本质特征之一。文人画作为载体,历来都承载了文人志士的自我心性和社会情感。他们常以笔代言,抒发胸怀,籍此作为言情达性的工具。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称《诗经》、《周易》、《离骚》以及自己的作品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文同曾向苏轼表露:“吾乃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谴之,故一发于墨竹。”而苏轼画古木竹石,只为一抒“胸中盘郁”之气。八大山人自题其画曰“墨点无多泪点多”,想其笔端,涕泪濡纸,他的寂寞无可奈何之境可堪一斑。大多数文人这种“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心态其原因多发乎“情性”二字,这种情怀在文人画中经过近千年的锤炼,已经成为他们表达思想,诉说情怀的必由之路。于是更多的艺术家在对现实的无奈之余把精神转向了山林,转向了禅佛,转向了超然于世,出现了大批的山人和居士,他们把追求绝对的精神寄托变成了他们毕生的生活理想和奋斗目标从而偏离了现实。
但“情感”并非超验的概念,作为人们对现实的一种批评性的反映,它在不同的画家身上体现的却不同。在霍春阳先生的画中,我们很少看见那种愤世嫉俗的冷漠和天老地荒的萧条。他的情怀正如他的名字:“春阳”,一如春天里的朝阳般温暖平和。他的情,是“静”不是“愤”,是“境”而非“荒”。他说:“艺术首先要净化自己”,“去掉一切私心杂念和浮躁气。”“只有保持了纯正纯洁、质朴的心态,才会排除世俗的污染,只留清气满乾坤。”他一直追求“无异言而生清净心”。只有不求异言,才能清静下来,才能进入一种“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的境界。在历代文人的心目中,荷花是高洁的象征。其“濯清莲而不妖,出淤泥而不染。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美好形象,赋予了画家取之不尽的灵感。霍先生笔下的荷花,虽多秋荷,但少有残败之象,正是“秋荷独后时,摇落见风姿。”他画莲蓬,题到:“莲籽得时依旧长,文禽无事等闲来。”一派悠哉游哉恬澹澹的景象跃然笔端。他在创作中践行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人格的修炼和锻造健康的心态成为他艺术实践的重要过程。记得霍先生在他的《双清图》提拔中写到:“兴来磨就三升墨,写得芭蕉和梅花。骨格纵然清瘦甚,品高终不染尘埃。”表现出了一个文人不入俗流、我之为我的品格。
在当代,似乎更多的画家仅仅是讲情感而已,却少有大情感者,这不仅是缺乏传统文化底蕴的表现,也是在把艺术创造与人生修养的结合上缺乏认识的表现。从霍春阳先生的“写意”中可以看出,在他的画面上融进了他对《周易》的理解,不仅有写,还有“经营”,。众所周知,《周易》表现的是宇宙万物的秩序,是本质性的规律。霍先生将创作情感引入到万物的秩序中,就是将小我融进大我,又以大我体现自我,从情意“悟处”着手,去营造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和情感领地。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内敛的情性落在创作上,就表现为主观融合客观,以情感再创意象,“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最简单的一花一草在他的绘画中,都以境界的营造融入了画家己有的思想和情怀,这样的“因心造境”,显示了画家厚重豁达的性格内涵和人格修养。
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是整体性的思维,即用所有的感官去感悟大千世界中的一切生命,然后再在“圆”的体系中宏观地把握最本质的东西。霍春阳先生的成功,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天分、勤奋、认识力、经验、环境,等等虽不可或缺,然更多地还是有赖于他对中国传统真正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他深悟所谓“珍珠虽小,鉴包六合;镜子再大,所照必偏”的道理,以为只有圆,才能通,只有通,才能天人合一,才能创作出自己达情顺性的作品,使自己的艺术有源有流。创作如此,做人亦如此,这也许就是霍春阳先生一生崇尚的艺术状态和生活准则吧。
赵星
2004年10月于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