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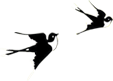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霍春阳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霍春阳 > 艺术作品 时间:2017-03-20 03:31:52
十三、由气韵非师而想到的
郭若虚是北宋外戚贵胄,也是深具学养的收藏家。他所提出的“气韵非师”是继唐人画论之后的又一真知灼见,他在《图画见闻志》叙论中开宗明义指出“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六法第一法即是气韵生动,唯此法必须是生而知之,其他五法皆可学而知之,这是人品使然。所以他又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而最打动我的还是“依仁游艺,高雅之情,一寄于画。”这是因果句式,细品其中消息,顿生隔代知己之感。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门教学之纲目,次第进取,不可割裂。有学者认为“游于艺”是君子志道、据德、依仁高贵而紧张工作之余的精神调剂,是一种玩玩的手段,大可不必认真。这是谬误至极的,一者尚未读通论语,再者没能深入理解孔学真谛。《礼记》学记对“游于艺”作了最好的诠释:“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再明白不过了,至道、据德、依仁都是学的范畴,而“游于艺”是趋于前三者的第一步或先决条件,用钱宾四先生的话说,艺是人生所需,人之习于艺,如鱼在水,忘其为水,斯有游泳自如之乐。“游于艺”不仅可以成才,亦所以进德,故谓其大人之学也。因此依仁游艺,即游艺所以依仁、所以据德、所以志道,否则文以载道,何以立言?譬如文字初始,依类象形谓之文,而后形声相益谓之字,遂成华夏洋洋之人文。孔子教学循循善诱,由此可现。绘画与书法是艺术,绝非技术,闲暇時之涵泳,投入时之唯美,它是纯粹的人格精神的自觉行为。因此先天的素质禀赋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精神境界之高下,郭若虚引西汉杨雄之言强调说:“夫画、犹书也,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又云:“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笔,所以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绘画的目的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实践,是心性和境界的展露过程。古人讲人品不高,下笔无方,人品不正则必露其形。人需要在精神上完备和圆满,只有圆满才能通达,具通达之心则有自在之态,有自在之态方能显自在之形。画者得之,识者未必知也,心正则笔正,大成功者不小苛,知大象者不繁杂。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好恶决定画品之高下,因此说画即是人。崇尚人品的中正,用正锋立正象则不朽,否则只是小聪明,观赵孟頫的山水画,山形皆中正之形,无奇峰与小情趣,马远、夏圭较之则为下焉者,更无石涛之奇崛,因此赵孟頫堪称宗师级之通才。因其观念中正,故而至美永恒。只有崇尚中正圆融,笔下形态始能涵容万象,终能一以寓万。古人讲与其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中正作人、立中正之象、写中正之字,书法的最高境界也是要使字复归平正。崇尚内涵者,才情不外溢,形色力神则不张扬,因其正大、所以光明。千百年来我们重复着孔孟对大丈夫的定义,而又践行了多少?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人格的至高标准,也是画格的准则。我们是崇尚精神完美的民族,人格的完美关乎画格的提高,特别是在当今媚俗多于典雅、庸俗多于高贵、恶俗多于清新的时代,面对大丈夫的定义,于人于画、于情于理,都该更具忧患意识。
十四、萧散简远和得意亡形
绘画至北宋各种题材趋于完备成熟,已达巅峰极致,甚难再发展。而苏东坡、米元章等人的出现却使中国画的走向峰回路转。东坡是位襟怀博大、性格耿介而又思辨前瞻的杰出人物,仅就其萧散简远的绘画理念谈谈我的看法,萧是一种静默的状态,如果繁则不会萧,如诸葛亮所谓“温不繁华,寒不改叶”是一种冷静的君子气象。散是轻松,不矜持,不鼓努为力,是静气平心下的随心所欲般的境界。简则是少而精,是纯粹率真,简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是以少胜多、言简意赅,是高度的提炼和概括,是一种最浑朴的包容。简则净、净则得、得则获,因此简是一种最完备的超时空的真诚。远是深度,是一种凝练而恒久的境界,合萧散简远而行之于画,则是古雅淡泊,得意亡形。东坡一句“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诗句奠定了几个世纪以来文人画写意论的审美基础,所谓得意亡形实则是把神韵放在第一位,以神取形,神动而形移;形是根据情感的变化而决定取舍,以情领形,意是不求颜色似,旨在赏意,形状要服从于立意、情感和神韵。中国的造型艺术要求妙在形外似、弦外音,亦可说是神似为本,形似为表,神似乃作者之神、主观之神而非客观之神、是情之神而非物之神,所谓物我两化,是以主观情感化育客观万物,大化之象是感悟众象之象,亦即感悟众象之常象,化为我情,由我情化育众情,是为常情。中国人以至柔为刚,故奉神韵为圭臬,而不以状物为准绳。更依常形常情之准,而非瞬时之情,也可以讲是大情寓小情。论画因何而“不似”,“不似”的过程,是看山而不是山的过程,看山是山,是由不似向真似的转化和回归,是返朴归真;以具似而含不似,以个别含一般,这就是雄伟出乎平凡、博大体现于精微、平和涵盖着奇崛的道理,所谓绚丽至极、复归平淡,极乎高明、中庸之奥,无不诠释着顺乎自然而形成的萧散简远、古雅淡泊所蕴含的真情实意。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有定力抓住根本,心不会摇摆,仁者乐山、厚重为本,智者乐水、深邃无涯,为人作画,此为根柢。
十五、平淡天真见古拙
米芾推崇“心匠自高”的文人意趣为绘画的至高境界,他提出的“意似”说与东坡的“写意”论可谓表里相承。米芾为人不拘礼法,每多任情骇俗之举,其书画及审美理念亦不循陈迹,妙气凌云。他对当时始终被漠视的董源、巨然的画风推崇备至,认为董、巨的作品不经意间透露出文人意趣的端倪,这在当时颠覆了上至皇室下至文人士大夫诸多既成定论的观点。他以“今人画不足深论”的狂语,宁犯众颜而一吐内心盘郁,足见其羞仰鼻息、不拾牙慧的傲岸风骨,他彪炳平淡天真的高古境界,在其“云山墨戏”的米点山水中得到了令后世折服的验证。高古是以拙示人,拙为朴,以朴为乐,素朴之美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谓朴实无华,豪华落尽见真纯,斯之谓也。朴实始可天真、天真才能烂漫、天真最终无邪;不张扬、不卖弄、犹婴儿之啼哭,如童言之无忌。故守其拙、抱其璞,真情源于此,是为赤子之心,是为全情;如朴为原木,破之为器,因此、子曰:“君子不器。”真情实则是无情,无情是厚道,亦是天道,天地无情故能化育承载万物而无声,江海无名所以成百谷之王,所谓上善若水,言其包容而处下。无情又是厚德,厚德故能载物,无求、无期、无意、最终无欺,才是纯情,因此诚恳。传统经典是艺术家的精神食粮,《论语》所谓:“素以为绚,绘事后素。”是平淡天真及古拙意境的最佳注脚。
十六、邓椿的贡献
“画者、文之极也”这句被后人泛滥引用的名句究竟蕴涵了什么天机?依我看来,他另外两句话说的比较明晰,“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说白了,绘画不能没文化;换言之、绘画是深具文化慧根,胸富学养的人干的事。因为绘画是文化者的赏悦之事,是思想情感和襟怀境界的表现方式,即文化的终极体现。较之以往成教化、助人伦、发明治乱的宣教功能,邓椿的见解则向写意寄情、抒怀明志的赏悦功能而转化,在审美理念上这是一种标志性的变革,为文人画逐渐取代宫廷画派起到了鼓吹激扬的作用。因此在其著述中出现的人物,亦如郭若虚所言,皆为“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之流,即名重生前身后的绝俗之士,邓公用心良苦矣。再者,邓椿把“气韵生动”来自于“传神”的概念,由人物画的局限扩张到世间物象之一切题材,万物之山水、花鸟等等,同人一样皆有情,能传众象之神,是真实意义上的“气韵生动”,对“传神论”与“六法”的内涵加以创造性的填充和大气的诠释,赋予六朝画论以新的生命力。中国画论自顾恺之以“传神写照”奠定了中国画的审美标准,至邓椿的“画者、文之极也”,可谓其尽美矣、又尽善也。正因在文化思想上的完备与成熟,中国的文人画,才能由宋人发轫、经元代大昌、越百世而不衰,这是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