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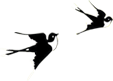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程大利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程大利 > 艺术作品 时间:2017-03-13 12:52:43
一
中国传统绘画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和陶融。刘勰云:“人文之始,肇自太极。”(见《文心雕龙》)由此而出发的中国画与其他民族的艺术拉开了距离。它的不重写实的“心象”观,强调人格品操的中正观和以书法入画的笔墨观都与西方造型艺术不尽相同。它虽不长于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变革,但仍表达着真切的生活感受和深刻的人生意义,它“内修心而外益世”。“抒胸臆而振斯文”,通过养心修身和知世悟道完成“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归于至善,“渡己”也“渡人”。
讲究“人”、“文”双修的传统中国画之所以不易于普及,是因为它对欣赏者有文化要求。“文”是进入中国画创作和欣赏的门槛。因“文”而“共成化育”,不是简学的“表现”、“再现”问题,是“体道义之合,究圣哲之蕴”,画画是为了修为,修成君子。中国画的最高指归是“内美”,屈原有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修能”就是为人格塑造。在中国画里,热烈不是宣泄,冷静不是冷漠,最忌高远失中、偏激不平;观通不妨照隅,求末亦是归本。这是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它的最大功能是让人静下来、淡下来、最好也慢下来。传统中国画从不表现争斗和血腥,却亲近造化,是自然的歌者。它追求至静至远,调和天人。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知识分子无论达或穷,书画都是修为的手段。
二
“逸”是宋之后,贯穿中国画精神的一个核心命题,如果仅仅把“逸”看作是“文人画”的产物,这认识是狭隘的。“逸”是笔墨文化成熟的标志。“逸”关乎才情,更关乎修为和境界。历来对“逸”的论述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不象——不愿拘泥于物象,“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实在是不屑于那个“象”。自由——忠实于个人情感。不做,不刻,不雕,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果做出来的也可能达到了“妙”和“能”,在流和做之间也能达到“神”,但“逸”必然是流出来的。出尘——与“意识形态”无关,不为谁服务,不为时风左右,不顾大众需求。当然它又绝然不是与社会对立,它是通过内省而达至善;人们欣赏它得先要提升自己,修养到一定的功夫,才能有所解悟。
三
气韵一词,最早见于钟嵘《诗品序》,内有“九品论人,七略裁士”句,“九品论人”是国家选拔人才时分人物为九品(见班固《汉书 古今人物表》),选才考试依据为“七略”(指刘向、刘歆所编诸子诗赋的总目)。由此形成了重视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世说新语》等书中有很多当时品评人物的记载。气韵一词最初喻人,后用到文章诗赋的品评中,如梁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气韵一词成六朝文化的精神所在。南齐谢赫在论人时也用了“气韵”一词,他在《古画品录》中评张墨、苟勖时说到“风范气韵,绝妙参神”,我们能由此想像出这两人的气质。在六法中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第一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在人物画发达的当时,人物的气质、韵致、风度、神采,乃至修养、性情均应是“生动”的。后来这个要求推广到对山水画和花鸟画的要求上,成为对画面境界的要求,经过自张彦远以来尤其是元明清以来历代评论家、画家的诠释,气韵生动成为对中国画的至高要求。但后人有气韵生动理解为技术上的墨法者,此大谬也。明唐志契在《绘事发微》中说:“画山水贵乎气韵,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间之真气。”故理解气韵生动着实须下番研究功夫。前人经验是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气韵者是不修、不做、不雕、不刻意,气韵是“创作”不出来的,是流露、是生发、是无意而为,如行云流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自然而然天成之物。气韵与急功近利相悖,与世俗也不相容。所以当下之“创作”,不见气韵也就不足为怪了。
汤用彤先生说:汉人朴茂,晋人超脱。又说: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画家当细细品味之。
四
明清以降,画论多为形而下的阐发,对技法的论述日益精细,成为审美经验和技巧的汇集。而早于此前一千多年的六朝画论则更倾力于艺术思想的阐发。再上溯至先秦,则是对艺术哲学的探究。老子《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出了中国画的本源在哲学。六朝的刘勰认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见《文心雕龙》)。太极之说见之《易经》,黄宾虹认为笔墨变化的一切规律均藏于那个太极图中。伏羲画卦见于《易 系》:“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俞剑华先生解读这段话是“实借种种思考经验而后逐渐发明以归纳成”的符号,这种符号“为宇宙万物之抽象表现,已具备后世绘画写生之法”(见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而对于“道”与“器”的论述,《易 系》明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艺术思想通达天地之道,最神奇的是一部医书中有画学思想。《黄帝内经》有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是画家的最佳状态,有通达天地的恬淡真气,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就不会被世俗的干扰侵害,画面会有清净感。《老子 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心灵静寂虚明,才不为外物干扰,从而洞悉造化本质,澄怀观道即为此意。老子接着又说:“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以为天下正。”这是中国画家的修为。认识到此即已不易,知行合一尤难。清人张式直接要求画家“学画当先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未有心不和平而能书画者”(张式《画谈》)。这样一来,对追求时尚成为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画的本旨已变成遥远而虚无的概念,今人若不潜心思考,所画者与本质意义上的中国画只能愈来愈远了。
五
石涛有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造成数百年之误读。笔墨当随造化,山水画的笔墨来自山川,而山水是永恒的,在这种永恒面前,人的所有活动都是短暂的。研究山川宇宙的永恒是人类始终的兴趣。其实这也是石涛的认识,否则何以有“一画”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见解呢?石涛力主“笔墨当随时代”,结果笔墨较之弘仁、髡残、八大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实际上是多了几分浮躁。他才华过人,留下不少好作品。但许多作品徒见个性,不见山川境界,或者说不见深邃的静寂,也鲜见笔墨的金石高趣,不少作品锋芒外露,处处机锋。石涛“丹青竞胜”“笔墨贪奇”,在传统画论看来,这都是毛病。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大受追捧呢?因为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是革命和批判,同时把西方传入的对个性的张扬作为首要标准,并视为时代精神。所以,石涛上人的缺点便被当成优点,甚至作为典范。今天我们看石涛还是“古之面目”,但少了许多简古平朴之趣。
六
自宋以来,中国画是在诗性的路上发展着。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抒胸中逸气耳。”这个“逸”就有诗性。从元至明、至清、至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中国画在“文人画”这条路上登峰造极。但20世纪以来,具体说,齐白石之后,诗与画逐渐疏离。画人国学兴致日减,画文人画的人逐渐离开了“文”,注意力放在图形、色彩和诸多科学手段上。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典型的中国人——即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中国人——即进步了的或者说是现代了的中国人。”
辜氏的话有两层意思:“典型的中国人”日趋消亡,幸哉还是不幸?按辜氏一贯主张,真正的中国人消亡是很可悲的。二是“现代了的中国人”如何保留自己民族的典型性,也即如何保留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将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七
如果说西方艺术作品中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张扬,比较而言,中国画把“人格”看得比欲望和本能更重要。中国古典文化的价值指归是“人格”,认为艺术应该为人格的完善服务。张彦远解释“骨法用笔”为“生死刚正谓之骨”,文徵明认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历来的画论都把人格因素与技术因素融为一体。可以认为,中国书论和画论都是伦理主义的艺术论,认为“文”是“心”所决定的,而“文”又可以用来养“心”,使“心”至善。人格文化的社会是“修身、齐家、治国”作为最高理想,人格文化的自然观是“天人合一”,相信“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且强调“顺天命”。后来冯友兰讲到“天地境界”,也认为天人的一致方可以达到至高的境界,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
笔墨之道通达“天地境界”。人力不逮处,即为“天真”——“天”之“真”,努力追求这个境界,不雕不做,朴素自然,感天地之化机,自然天成,这便是笔墨的至高境界。笔墨之境岂止是苦练所得,更是“修为”和“蒙养”的结果,不只是技术之境,更是人生之境。
八
中国画家必须读书,而且要学会读书。
古来学问家都是会读书的人。读书有道,读书可以把穷理尽性,把读书和变化气质联系起来,人则会不同。而把读书与体验证悟和涵养功夫联系起来,笔墨会日进。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读书性》写道:“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读书在于穷理博文,他进而说:“必涵养纯熟,然后气自常定,理自常明。逢缘遇物,行所无事,毫不费力。然其得力处,皆在平日读书穷理工夫不间断,于不知不觉之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气质自然清明,义理自然昭著。”又说:“读书非徒博文,又以蓄德,然后能尽其大。盖前言往行,古人心得之著见者也。蓄之于己,则自心之德与之相应。”马先生把读书、明理、养心结合,道出了读书的要诀与规律。前人认为,读书多了,笔下俗气会褪,所谓“书卷气”是读书涵养的功夫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读书不一定马上能用,不必立竿见影,是日积月累的涵养功夫。
画面上的书卷气是读书的结果,而不是苦练所得。
九
六朝的宗炳对赏画和作画的快乐的描述是生动而富深意的。他说:“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熟有先焉!”
这里的“闲“字,是笔墨文化的要求。“闲”是解除心累的良方,“闲”、“散”、“静”、“淡”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功夫,在这个状态下才能产生“神思”——思想的自由与深邃。齐白石老人刻了一印,曰“一闲对百忙”,乃彻悟之见。
“山水”相对应于社会,宗炳生于思想自由的六朝,向往山水多少隐含着对世俗生活的疲累与无奈。到了北宋郭熙,直接认为“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山水画,被历来的士大夫文人看成是离世出尘的方式,以此涤滤身心,求得安静和端详。近百年来,这种出世的倾向被赋予消极的意义。山水画在“入世”上下足了功夫,贵五彩,重形似,与照相机争功,很长一段时间,本质意义上的山水画被“时代精神”异化了。进入山水,大多为“仁”、“智”所驱,求山水本真,绝非找山水的“时代精神”。山水永恒,抱恒守一。虽然,今天的生存环境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差异,但对自然的向往是人的本性,与之和谐也将是所有文化的共识,“心源”中的山水永远都是远离尘世的平淡天真。画山就是画我,“我”自何来?来自山川。
十
钱穆先生说,中国思想之伟大处,在其能抱有正反合一观。如言生死、存亡、成败、得失、利害、祸福、是非、曲直,莫不举正反两端合为一体,其大者则如言天地、动静、阴阳、始终,皆是。(见《中国史学略论》)
而中国画的笔墨辩证关系也是正反合一观。如黑白、虚实、浓淡、疏密、奇正……以“实证”的方法,看不出中国画的好和不好来。全部的辩证关系的微妙处理就会画出好画。最重要的是,中国画有“内美”之求,“内美”来自《楚辞》——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宾虹老人说:”画中内美,非常人所能见“。看来懂得内美不是易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石涛活学了老子思想——“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把所有辩证归一。
程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