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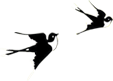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王鲁湘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王鲁湘 > 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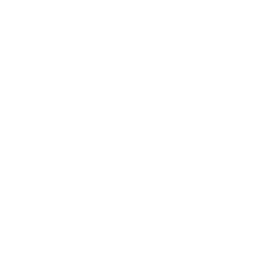
时间:2018-01-05 02:08:08
一、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腾讯文化:你从一个拥抱西方文明的年轻人,到开始决定要去发觉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胎记,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王鲁湘:很多人把《河殇》表现的文化观就看成是我王鲁湘和苏晓康的文化观,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河殇》的文化观带有很强的策略性。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策略:通过鞭笞自己的祖先、传统和历史,憧憬甚至夸大西方文明的优点。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们想要那个新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批判上的策略安排,就像女权主义一样。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人类历史,很多转折点、交接点上产生的思想,某某主义等,其实是一种策略。
腾讯文化:也就是说你在写《河殇》的时候,内心并没有把中华文明的衰落完全归结于整个文明的基因,对传统文化并不是抱有敌意的。
王鲁湘:对,《河殇》是要经过中央电视台审批播出的,我们其实在写这个文本的过程中间,更多要讨论的是现实,但是我们不能说呀,我只能越过现实,跑到前面,本来是父亲的错误,我们就一定找到爷爷,说爷爷不该干涉父亲。
腾讯文化:你对传统文化一直是关注的,并不是后来才认识到它的价值。
王鲁湘:是的。因为我在北大读的专业就是美学。实际上是之前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意义没有那么充分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当时的开放度不够。其实只有最大限度的开放,才能最大限度地认识自己。
腾讯文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发展的现实是不是印证了你当年的推论?你对中华文明发展方向的立场有变化吗?
王鲁湘:人类历史有很多无奈的事情,思想往往走在实际的前面,因此这些思想者往往会变成殉道者,因为他们的声音是超前的。我们现在都说“中国梦”,其实当1988年《河殇》播出的时候,之所以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刻,理论有多么新颖,其实倒不是如此,整个《河殇》用六集建构了一个梦,然后鼓动中国人民去寻找这个梦——现代文明的梦,这个现代文明的梦为我们设置了一个取向,就是海洋,海洋象征着开放,就是人类最先进的文明。
所以,我们第一集叫《寻梦》,第六集叫《蔚蓝色》,就是一个蔚蓝色的梦。你这个年纪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见证我们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就在用30年的时间在寻这个梦,基本印证了《河殇》的推论。
腾讯文化:你觉得这样一条发展之路是否是一条正轨?
王鲁湘: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现在是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以后的历史只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为什么没有错?判断标准非常简单,不需要纠缠历史细节,我们主要看基本的一个态势。
1949~1979年的中国历史,是一个越来越封闭的历史,以至从治国者到普通老百姓,六亿人民净愚人。1979年以后到现在这36年,至少它是一个开放态势,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间不断有封闭和开放之间的较量,两种力量的纠缠与博弈,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至少有一点,它再怎么博弈,也没有改变这个开放的态势。
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如此了解过世界,如此走近过世界,也从来没有像这样站在世界的立场来认识自己的历史,过去我们是没有这种视角的,也没有这种视点。所以这个历史趋势证明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错的,我们讲开放。我曾经在好几个地方做演讲的时候,都提到过一点,对人类来说,对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文化来说,它最可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不是它已经创造的所有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甚至也不是它的国家,它的信仰,而是开放。
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哪怕它遭遇了非常重大的天灾人祸,把他的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的积累破坏得所剩无几,这都不要紧,它只要是开放的,十年左右就能恢复元气。为什么?开放的空间有无数信息的交流,这个共同体就会处在一种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说的“熵”的状态,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机体,这个活力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创造力,新的东西就会被创造出来,它就会取得非常神速的历史进步。但是如果这个共同体已经创造了非常丰厚的历史遗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的物质的文明的财富,只要它一封闭,20年,所有的人都变成愚人。
腾讯文化:但开放容易带来矫枉过正,人们觉得“中国不像中国”了。因为我们过于拥抱西方文明,我们摒弃了一些固有的东西,我们自己的很多文化传统都没了,让大家感到焦虑。
王鲁湘:美国有一个人类学家曾经在《纽约客》上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做《我们是美国人吗》,他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用第一人称来写他这一天当中所有的活动,结果这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地揭示:一个带有浓厚民族主义思维的所谓“爱国者”,其实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属于美国的。床、镜子、出门戴的帽子、拿的手杖都不是美国的,花钱买的早报不是美国的……然后所有的一切,其实没有一样是所谓“美国创造”的,美国人只不过在享受整个人类文明的成果。
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所谓“国粹的中国人”是不存在的。
腾讯文化:但我们有些文化主体性的东西会丧失。
王鲁湘:对,讲到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确实也知道,开放、交流,会带来改变,改变会使我们变得不太像过去的自己。但是这种丧失是一种“建设性丧失”。比方说我们拿一个人的身体来说,他从出生到长大,这个成长过程中间,一定有丧失,但这种丧失是成长的代价,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很多东西就像水一样,流动的时候是活的,不流动时就是死的。文化其实也是这样,从来没有固态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动态的,像水一样不断地变形,这个没有关系。
腾讯文化:这些年里,你一直在关注传统和现代性的兼容问题,对此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王鲁湘: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有普世价值存在,如果没有普世价值,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人类这个名词,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逻辑问题。人类这个词如果成立,就一定还有一个词组群,从各个角度来定义它,普世价值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定义。没有普世价值,人类这个词都应该从辞典中间取消。
我们要解决一个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对关系——群己关系。中国过去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国家制度是在宗法、血缘关系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制度在涉及群己关系的时候,有一套完整的设计,但当它面对一个更加开放的城市文明时,这套建立在血缘关系中的村舍中间的群体关系显然不适应陌生人之间了。所以我们就要重新进行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社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建立在新的工商城市社会上、陌生人世界中间的一种群己关系。
那么我们过去,我觉得在这点上,设计的是有一些问题的,这就涉及到民主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每一个人应该是自由的,个人的自由权利是必须有法律给予保证的,而且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些权利包括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但是这些一个一个的自由在一个群体社会中间的时候,它是被设定在关系之下的,这个时候的关系就得通过民主来解决,它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公权力和私权力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这个关系的设定处得不好,我们就一直跨不过传统社会这个门槛,就进入不了现代社会。我们儒家对上古社会的憧憬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虚构,仅仅是拿来对当下的现实进行批判的,在操作层面上处理得比较好的还是西方、欧美。
腾讯文化:你怎么看待年轻时候的那个王鲁湘?
王鲁湘:还是那句话,失去的是“建设性丧失”,我自己叫做“建设性成长”。肯定过去的自己,接受现在的自己。对于《河殇》作者个人的命运来说,我们似乎只是建立了一个玻璃屋,这个玻璃屋很容易地就被人击个粉碎,而且掉下来的玻璃茬子还把我们扎得满身鲜血。但是这个不重要,思想史上、文化史上,这是思想者和文化人的宿命。他必须在历史的进程中间,承担这种先知先觉而带来的所谓“殉道者”的历史角色,他必须要承担这个东西,不能抱怨。
二、“我不是辜鸿铭”
腾讯文化:你现在关注的问题完全转移到传统文化上来了吗?你觉得保存传统的意义在哪儿?
王鲁湘:我不想被人解读成一个所谓的“国粹主义者”,我仍然是一个思考现代化问题的知识分子,我永远不会是一个像辜鸿铭那样,站在国粹的立场上对现代化坚决排斥的学者。
我对传统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思考中国的现在,或者是思考人类的现在。这句话说得有点大,实际上回到20多年前《河殇》的时候,那种对传统激烈的批评,对于现代化、现代文明的无比向往,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对自己的传统不够了解,不够深入。
人类总是带着自己的胎记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胎记就是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总是带着自己过去的记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对自己的了解非常肤浅,你很可能就把一些对未来有很重要价值的东西抛弃了,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在河南新郑的祭黄帝陵的大典上,我曾做过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祭拜黄帝的演讲。因为我从历代祭黄帝留下的这些文献,特别是那些诘屈聱牙的碑文、祭文中间发现的是像《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所追求的价值,它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其实就和法国大革命时对人类的理想的描述、美国开国元勋对美国社会的憧憬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把它们看成是糟糠,弃之不顾,是因为我们觉得古代的那套语言没有办法接受,当你一句一句地把它变成现代白话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头充满的是崇高的、美好的、人类的梦想。
有很多人觉得我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喉舌,一直在呼吁保存某些民族文化记忆的东西,这和我前面所说的这种持开放的文化立场,其实并不矛盾。我们都是人,一定有我们人共同的东西,但我们每一个人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才是真正活着的人,而不是机器人、基因人。为什么?就是个性,个体化的存在,它使得这个世界具有多样性,而多样性恰恰是一个生物种群能够健康地生存下来的一个条件。我们在大自然中发现,凡是这种生物性单一的地区和群落,它的生态都是最脆弱的,而这种生物的种类越复杂,越丰富,它中间一些神秘的相关性和联系性就越多,这个生态系统就是越结实。
腾讯文化:所以您做一些保存传统文化的东西,是为了这个生态系统更多保存一些个性的东西?
王鲁湘:对
三、“风水”与“先生”
腾讯文化:有时候会觉得《文化大观园》怎么什么东西都上?怎么风水这些东西都会上?
王鲁湘:有。第一个讲风水的是在我的节目里,因为我一直认为风水是一种文化,几千年来,它渗透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间,方方面面。有些人会把它讲得神神秘秘,有些人会看到其中合理的东西,尽量地用一种现代科学的理论来重新解读它。
其实在我的节目中,我一直试图客观地呈现,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个东西,电视为什么不去碰它?我把它先客观地呈现出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东西本身没有多严重的伤害性。
腾讯文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有伤害性。你以一个客观的态度呈现了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是传播的效果,实际上是不能控制的,你会有意地在节目中做一些风险的规避吗?
王鲁湘:我认为不好的东西,我坚决不会做。比方说在春节期间,有好几次让我采访香港所谓的“运程大师”,那我是坚决拒绝的。风水我为什么会做?因为我觉得风水有很多地理环境的东西是有味道的,但是纯粹所谓“算运程”,我觉得在我节目中是不能做的,我觉得我还是有底线的。
四、一个温和的改良派
腾讯文化:在大众看来,不管是语言,还是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你都比《河殇》那个时候克制了很多,即便是在介绍传统文化的时候,也没有过多地去干涉采访对象。你觉得文化的节目不需要投入很多主观情感吗?或者说是有意在克制。
王鲁湘:其实凤凰曾经希望给我量身定做一档更有文化批判精神的节目,以一个纵横捭阖、议论横生的“文化批判者”的形象出现电视屏幕上,用更犀利的语言、更具挑衅性的姿态、抛出很多具有争议性的东西以引起注意,让节目迅速地红火起来,但是我自己坚决反对,不做这种类型的节目。
腾讯文化:你有的时候还会参加甚至是主持恢复祭孔,你觉得那种形式有必要再恢复吗?
王鲁湘:有必要。有些传统的文化的形式的革除就带来内容的革除。按照西方的这种二元思维的模式,我们都把内容和形式看成是一个二元性的东西,所谓“内容决定形式”。其实这是不对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很多形式的恢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内容的恢复,比如说一些宗教祭祀的仪式,我们过去认为它就是个形式,其实不是,这种仪式本身带来的人的庄敬感,就是庄严、敬畏的感觉就是内容。
腾讯文化:祭孔这些仪式的恢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重塑人们的庄敬感吗?
王鲁湘:恢复的内容不仅是庄敬感。比如我们一些祭孔形式,能把我们带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已持久发生精神指导作用的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去,让我们通过一些仪式去接近古代的圣贤。让我们知道这些古代的圣贤不仅存在于文献和书本上,还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很多习俗中间。只有在社会生活的习俗中去实践圣贤的文化设计,你才能够真正去理解它,你就能够透过这种文化,更深入地理解人的境界的高和深。
现在我参加很多的《论语》读书班,最小的5岁,最老的80多岁,大家在一起共同学习,不需要很长时间,十天半个月,整个人都会改变。
腾讯文化: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种“戏仿的滑稽感”。如何让这种庄敬不被消解?
王鲁湘: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某些人的感觉来替代另外一些人的感觉,比如说同样在曲阜孔庙祭孔的时候,参加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感觉:有些人非常投入,整个过程对他来说是人格的升华和精神的洗礼;有人觉得这是在演戏,这个戏还很滑稽可笑,他们在旁边会不断地发出冷笑,甚至会义正词严地写批判文章,来批判所谓的祭孔仪式;有些人不置可否,他觉得这个事情可以中性地对待。不同人的感受你应该被尊重,那是他自己真实的感受。
之前在凤凰岭的拜师典礼,被很多媒体一边倒地进行口诛笔伐,变成了一个网上恶炒的一个现象,认为是一场滑稽戏,认为在人类进入21世纪文明的时候,竟然还有这么愚蠢的、愚昧的行为。其实这个事情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天天都会有师父在带徒弟,不管是梨园行也好,或者很多民间工艺行当。我们只不过是因为有十几个导师收了几十个学生,开学当天举行了一个集体拜师典礼,很多人通过图片看到千里之外一群撅起的大屁股,觉得滑稽可笑。殊不知在现场气氛严肃庄重,无论是导师还是跪下去叩头的学员,还是我们邀请观礼的嘉宾,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我们当时没有想让这个活动会产生多大的教化力量,我们只是想做一个实验,就是说通过这么一个拜师礼仪,能不能改变一下我们现代教育的师生关系——一种简单的知识传授关系——能够引入更多的人文的、情感的内涵,让师生关系不要那么功利和冷漠。
在没有拜师之前的时候,这个导师和学生之间就是非常客气的,功利的,我给你上完课就走了,你和我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拜过师的老师和学生,就有点情同父子,那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尊敬,包括技艺传授之间是否有所保留,就不一样。这个好像是那种人情的东西,很神秘,但它能够让人感动。
腾讯文化:如果说你想把这种神秘的体验传递出去,但是在决定要做这个事儿之前,其实你是考虑到了可能的传播后果?
王鲁湘:没有,完全没有。我们觉得这是没有多少炒作价值的东西,如果说放到十年二十年以前,它有很大的炒作价值,但是现在拜师礼仪非常普遍的情况之下,没想到变成了那么大的媒体传播事件。这种宗教性质的仪式,我们的经典里把它叫做“神道设教”,过去唯物主义的思想统治之下的时候,人们被唯物主义洗脑,你就会把所有的这一类的问题都叫做神道设教,而且只要是神道设教就是愚民政策,就是愚弄百姓,其实是不对的。
腾讯文化:其实是跟之前《河殇》一个概念,就是吸引大众眼球,制造一个话题,或者把一种观念炒热。
王鲁湘:《河殇》只是一个作品,而且是一个集体创作,但是我要做的栏目是一个持续很多年的个人讲坛。
首先你一定会透支,因为你持续地输出观点,怎么可能?如果你为输出而输出,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我不觉得出于收视和商业目的的文化观点不断地、所谓地创新和输出,其中会有多少诚意。
其次,这个其实和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其实是一个很善于倾听的人,我在我的节目中扮演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你倾听得越多,你就会越来越质疑自己“质疑的能力”,你到底有多少知识储备能去不停地质疑不同人的观点或者信仰?其实对方只是在谈他相信的某一个东西,那么如果这个经验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过,那么你哪儿来的质疑能力呢?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能倾听。
腾讯文化:单单从节目的形式来讲,你觉得现在对于唤起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这种文化批判类型的节目需要吗?
王鲁湘:非常要。我从90年代开始就曾经和一些非常激进的学生说过,现在已经不是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阶段了,我们现在需要专业的知识。
腾讯文化:为什么现在不是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阶段了?
王鲁湘: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孙志刚事件被网络和媒体曝光了以后,他真正带来的历史进步,不是那种站在道德高度、思想高度或者文化那种笼统含糊的立场上的评论,而是非常具体的专业讨论。为什么收容制度是不对的?在法理上它错在哪里?中国社会从90年代以后取得的每次进步都是小步前进,它和80年代大不一样。
整个80年代是思想启蒙、文化启蒙的时代,那个时候都是非常笼统的大话题,它带来的思想解放是大跨越式的。但进入90年代以后,真正能够发生并为民众、甚至是体制内的顽固力量共同接受的问题,都是技术上可操作的启蒙,然后社会开始小步前进。
《河殇》那个时代是猛击一掌,整个民族向前一跃,但是这个过程过去了,我们已经从封闭社会进到了一个开放社会。在开放社会,我们需要讨论、发表的是更加建设性的、可操作的技术建议,通过这种无数的小启蒙,使大家都回到真正的常识。
腾讯文化:这种“小步前进”也能算是一种启蒙吗?
王鲁湘:这也算是一种启蒙。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讲“建设文化产业”,我们突然发现,偌大一个中国,并不拥有人类最有价值的艺术创造品。当有一些人斥巨资从欧洲、美国购买回来毕加索或者是欧洲古典主义时期很著名的艺术品的时候,被我们莫名其妙地超高关税挡住了,使得中国人民不能拥有人类创造的最优秀的精神产品。这时候就需要有一批研究税法的专业学者,咱们平时觉得他们跟启蒙无关,但是他们这个时候的发言就是启蒙。
腾讯文化: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如果文化批判这样的节目有必要存在,原因是要有这种技术层面的小启蒙。但是作为文化来讲,它可能涉及的问题更多的就是伦理上、价值上的大判断,这不是一个矛盾吗?
王鲁湘:这不矛盾,其实这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启蒙,我们现在还有,像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还包括所谓的毛主义论证,在某种意义上它就不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它仍然还是在思想启蒙的层面,但是我对于这种争论不太有兴趣。其实我们通过一个一个小启蒙,是完全可以打开民智的。
腾讯文化:那这个存在的节目的形式就不是一个文化批判的节目,而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
王鲁湘:对,各种类型,分得非常细。你现在打开网络,打开电视,其实都是非常窄的领域上、论坛里,很多专业人士发表非常专业的观点,这些专业的观点是真正具有启蒙意义的。
腾讯文化:实际上就是把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分散了,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全部都变成主持人参与讨论。
王鲁湘:对。那种所谓“登高一呼,万众云集”,不要想这个了,不需要。
腾讯文化:在《河殇》里面你也举了严复的例子,无论是在每个时期,每个优秀的、最开放的、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最后都会退到儒家的形态里面。你会这样吗?
王鲁湘:我也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对严复有一些误解。从严复到五四,很多西方的糟粕也被介绍到中国来了,但是严复的选择,我认为到现在都是最深刻的、对中国社会最有建设性的。这种思想本身就说明严复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他希望社会用最小的震动、最少的代价,取得最扎实的进步。这种性格的人进入老年,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会变得特别温和,充满着人性的温暖,你觉得他这个人都没有棱角,没有光芒了,就像一块玉一样,而且是一块老玉了,很纯和的境界。这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是他的社会角色可能已经变了,他已经在社会上退居边缘了,本身就已经边缘化了,他年轻的时候多少地在这个时代的中心,现在他可能就已经被一些新进取代了,于是他就会“退而修其身”了。我肯定会这样。
腾讯文化:你也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
王鲁湘:我应该就是,我觉得我是。
腾讯文化:《文化大观园》做了将近10年了,你觉得像传统文化的话题,还有必要做爆炸性的东西吗?
王鲁湘:没有,不可能。
腾讯文化:是没必要还是不可能?
王鲁湘: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腾讯文化:你觉得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东西?
王鲁湘:在开放社会里其实是没有爆炸性的东西,信息高度披露的情况下,没什么可爆炸的。爆炸性的东西都产生在封闭式的环境中,因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比如说《河殇》在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时候,产生那么大的所谓爆炸力,就是因为收看它的观众和这个节目之间有极其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腾讯文化:那你觉得在一个“需要小启蒙”的时代,文化节目主持人的使命是什么?
王鲁湘:我更多觉得平淡才是真。我不希望一惊一乍的。我越来越觉得文化是一个熏陶的东西,它看似好像是点点滴滴,平平淡淡,但是呢,但是就像和风细雨一样,慢慢地去影响,去改变,这是一种更好的感觉。所以《文化大观园》还是会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知识的出口。
腾讯文化:你以后更多地投入到这种私人领域,或者说是这些实体的建构吗?
王鲁湘:我肯定有一天一定要从这样的一个公众视野中间抽身而退的,这是肯定的。我自己是希望我60岁正常地退休,但是从凤凰现在的情况看,好像还不会让我这么自由地淡出。因为凤凰还要这样的节目存在。如果节目取消,我不会像有些节目组的人会铺天抢地地去争取自己节目的存在,也不会去给这个节目争取最好的时间或者更多的时长。
腾讯文化:所以顺其自然?
王鲁湘: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