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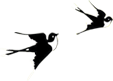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赵跃鹏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赵跃鹏 > 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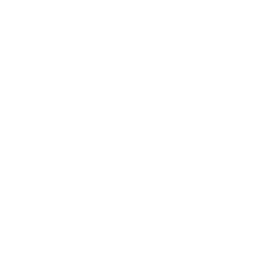
时间:2017-03-06 01:38:08
赵跃鹏在公众聚会时往往是不多言辞的,但这并不证明他不善于表达。他对绘画的理解,对宋元的继承,对明清大写意传统笼罩下的当下画坛的认识,足以让他的言论有了某种思想的深度。
他关于“画家的成长是一个自我妥协过程”的理论很让人启发,同时也让人看到了他不愿随波逐流的个性和不愿趋同的笔墨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陈传席先生 看到他的作品时候“是古人还是今人”的惊呼。
还有一点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自己很懒,以致于很少画画。能这样剖析自己的人不多,能深刻了解自己需要什么的画家更少。赵跃鹏的“懒”是基于对自己的深入了解,明确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懒”也不怕。
时间:2009年5月5日
地点:甘棠馆
受访:赵跃鹏
采访:鲍洪权
鲍:1990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以后你在干什么?
赵: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以后,我去了青岛工作。之前三年级下乡写生的时候去过,对青岛的印象挺好,所以毕业就去了。去了之后才发现并不习惯,感觉那里对浙江美院毕业的学生相对比较排斥,我又不太爱交际。两年后我就调回杭州,把关系挂在浙江教育学院,我自己在社会上玩了几年。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与画家圈接触,也很少画画。
鲍:之后还去过皖南?据说还玩古家具?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赵:我是1997年的时候去的皖南。怎么说呢,我这个人有种怀旧的情节,对老旧的东西比较喜欢。后来有一个机会就去了。去那里住了几年,很喜欢那里的文化遗存。那里的山川风物与浙江差别挺大,我们所知的徽派建筑石刻木刻当时还保留很多。在那里见了不少民间优秀的工艺作品。总之,那段时间人很快乐。
鲍:你刚才谈了那时候几乎没有动笔,这对一个画家来说比较特殊。怎么会不动笔?印象当中热爱艺术的画家是每日临池不缀的。
赵:我做事情以兴趣为主,我自己不是一个在专业上有使命感的人。就说画画吧,觉得没有兴趣的时候我就暂且不画,那段时间我画画也很少,几乎没怎么动笔,因为没有兴趣,我没有太把这个东西当职业。虽然实际上就目前为止,我的职业是画家。还要靠画画生活,这是事实,但是我个人还是将之视为兴趣的一种,我觉得把画画当职业感觉挺累。我是一个经不起被“逼”的人,或者是一件事情让人们逼。那样我会觉得特别累。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应该环境宽松,这样也才有可能做好。
鲍:后来还考了研究生。
赵:是研究生课程班。当时态度也很随意。也是有朋友一起来。说我们一块去读。并没有事先有什么样的准备,或将来的设想。
鲍:经历对一个人的思想和成长都有极大的影响,你怎么看以前的经历对绘画的影响?
赵:我不知道到底有么重要,或者说影响有么多大。但或多或少肯定是有影响的,但要说对我的绘画带来特别大的影响,我觉得不是。起码对我来说,没有那么严重。有可能的话是人变得略宽容了些,包括对所谓“艺术”的主流非主流风格不再那么在意。
对画法我不太在意手段上的“正规”,但有“格调”上的要求。
鲍:眼高手低是正常的,往往难的是眼高、手也高。
赵:眼高是手高的基础,起码有成就者都是从这个过程过来的。有些人眼光起先还算“挑剔”,但在过日子的过程中降低了自己的要求。人的成长过程也常会变成一个妥协过程。开始选择的目标都挺大,选择的东西也挺好。但时间长了以后,会认同,会妥协。画家里也有人会这样。变得容易容忍,认同周围不太好的东西。原来觉得很差的东西,最后觉得还不错,这是很可怕的。
鲍:要做到不妥协也很难。
赵:我觉得作出选择是最重要的,人不媚俗,很难做到。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只要有正常人的智力,做什么都可以成为大师。
鲍:我们继续聊画学,“道贤画学中兴”之后形成了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大写意一路以外,一直也不缺学宋人的典范,比如张大千、吴湖帆都是学宋人的典范。学术界也一直强调要回到宋元,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回到宋元。我不知道这口号出发点是什么。中国绘画到目前为止宋元的技术含量是最高的,就绘画性而言是最完整的。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个毋庸置疑。
现在人讲回到宋元,怎么个回法呢?大家可能觉得现在绘画颓废了,我们在技术上要回到宋元时的严谨,宋元时那种对待绘画认真的态度。这是对的。从态度上认真对待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是对的。但如果说我们回到宋元的绘画形式上去,这就显得有些背时。现代人可以画现代人的东西,如果要说“我这一笔,是宋代人用的一笔”,“这个构图是出自某某构图的要求”,我觉得这没有意义,很无聊。
我之前也跟人家说起,继承传统有符号性的继承,还有精神性的继承。你选择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回到宋元关键应该是对于绘画态度上的问题。
鲍:你刚才谈到的宋元问题可以归结为“从精神上回到宋元,而不是说从形式上简单的复制宋元。”
赵:因为大环境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居生活所依赖的农耕社会的大环境已经变了。
即使我们还学古人吟风咏月的生活做派但也已比古人多了许多其它的牵挂与关心。反过来说,我们每个人又都生活在这块地方。无论受传统教育多少,都多少沾染着本土文化遗留的生活习惯与审美态度,这是不可回避的。其实,我们要做的是理清自己的思路,画画要有个认真的态度。摘的太简单或太复杂都没必要。
鲍:陈传席先生说你的画“绕过明清,直接取法宋元”。长期沉浸在宋画的环境里面,是不是有很大的磁力吸引着,然后是被“罩住”了,跳不出来了?
赵:喜欢肯定是的,但是我有自己的念头,怎样走自己的路本来就是很自由的事。我是个很懒的人。因为懒,所以即便在学习宋元,也不愿在纯技术上下太大多的功夫。我更喜欢在意宋元人作画时所持有的态度。
如果评论家认为我有自己的面貌的话,这跟我对绘画作品表达的气息有很大的关系。喜欢冷峻萧疏的东西,不喜欢那种大红大绿或过于热闹的作品。比如我不喜欢“四王”,单纯从绘画程序上来说,“四王”有些作品还算不错。但对比清以前人的好作品再回头看“四王”的画就没有意思了,“四王”没有创造性,作品给我的感觉跟熟练工人手上做的活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作品或比许多纯画匠要“雅”些,但我认为还只是干体力活的。只是换了纸上作业罢了。“四王”的作品气息只是旧,没有高古感。那种温吞水的平和很没生气,作品内容的千篇一律只让人觉得他们很有耐心。这样的追古我觉得是没意思的。
鲍:聊聊你对绘画的进一步认识?
赵:我从读书开始就没有喜欢过“四王”。开始喜欢“扬州八怪”,结果后来也不喜欢了。原因是觉得他们画得太随便(华碞除外)——文人画发展到后来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不注重作品纯粹的画面视觉完整,过于依赖着一种情绪一任放肆,失去了作品技术层面的严肃性。我觉得这是中国画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给后人对国画的赏析带来了一种误导:好作品都是一挥而就不加思索的。严谨的东西就是“匠气”。
鲍:有很多评论家说你的画属于“飘逸”一路,你学的宋画是严谨的。严谨跟飘逸是两种风格,在你自己的绘画作品中,两者有冲突吗? 赵:严谨与随便是两回事。“飘逸”不单只有随意,我画画一直是很认真的。关于造型、用笔等我在我的理解上是在尽力严谨且有个达标的范围,但我画上的时候有很放松,很少有很“累”的状态。
鲍:刚你谈到你的“懒”,给我的感觉有两个层次:一你很有天赋,疏于勤奋地练习;第二你是真的懒。是否是我想的那样?
赵:我是真的懒。但我也认为绘画不是每天关在屋子里面就能画好的。不想画画的时候,硬画是没有意义的,但在作画的过程中我会非常的投入。之所以不天天那样画,也是希望不要把自己画麻木了,画得没感觉。当然这也给我自己的懒散找了借口,使我自己变得更懒。
喜欢做一件事的时候,肯定能投入比较好的精力,包括情绪,这个时候成功率就比较高。
鲍:你怎么看“浙派”?
赵:就风格来说,浙江画家每个人之间风格差异还是很大的,现在人说起的“浙派”已与以前的“浙派”不是一回事了。原来的“浙派”更有一个较明显有别于其它画派的风格。现在只是因中国美术学院的传统教学影响下浙江画家相对外省画家的作品显得较传统而已。但在传统范围内还是风格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