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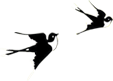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何加林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何加林 > 艺术作品 时间:2017-04-19 02:06:43
何加林是才情出色、根基好的画家。所谓“根基好”,指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曰对中国画的认知,二曰笔墨功底。试作释说:
中国画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独特的民族形式,对它缺乏应有的认知,就无法悟其真谛,辨其优劣,登其堂奥。由于20世纪美术学校采取西方模式,中国画教学对自身的认知问题始终被漠视,学生不熟悉画史与画论,学中国画而不理解中国画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认知的不足带来了严重后果:盲目以西画观念代替中国画观念,常常以粗暴的态度对待中国画传统,鉴赏力贫乏,没有充分的自信。当然也有例外,最突出者便是以潘天寿、陆俨少为中坚的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他们培养的几代人,从方增先到陈向迅,对中国画的认知就大不同了。更年轻的何加林、张捷等,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我读过何加林的一些文章和谈话(如毛建波《何加林访谈录》),对他的思考颇有印象。他认为中国画家要有一定的“国学底蕴”;要“静下来对传统文化进行思考”;他要求自己在实践追求上“纯粹不杂”,但不过早地“定型为某一种风格”;他重视对经典之作的临摹研究,但又十分重视写生,探寻以新的方法“表现自然界的勃勃生机”;他有意在疏离传统与回归传统之间“反复”,并把这种反复作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这些,都体现着他对中国画传统与本质特征的深入理解。理性思考代替不了技巧训练,但有没有这种自觉思考,有没有中国画的自觉意识,是大不一样的。
“笔墨功底”是老话题,也是常新话题。作为形式语言的笔墨,决定着中国画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绘画的根本标志。趋向多样发展的当代中国画,除少数边缘形态的“实验水墨”之外,都没有或没有完全脱离笔墨。在西方强势文化铺天盖地而来的今天,怎样对待笔墨,关系到要不要坚持中国画民族文化特色的问题。但在艺术实践中,关键不在笔墨的使用而在使用得怎样,在是否真正得到了笔墨的真谛,使它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因此,笔墨基本功的修炼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美术学院的中国画基础课,着力点正在笔墨训练。何加林在新时期接受本科与研究生教育,教师的指导与他的选择都具有很高的自觉性——临摹多而系统,目标明确,主动性强,这一特殊环境条件加上出色的个人条件,造就了他在笔墨上的良好功底与相对早熟。
何加林把自己的作品分为两个阶段。1999年前为第一阶段,“大多表现儿时生活过的西北”,“是艺术与技术的磨合期,从浓墨时期,走到干墨时期,走到淡墨时期,偶尔画些青绿。”1999年春至今为第二阶段,“主要以江南山水为题材,捕捉江南的泥土气息”,“全身心投入写生,几乎忘了所有的技法,从中又得到了许多传统中得不到的东西。”(《给笔者的信》,2001年11月l8日)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何加林》,大抵代表第一阶段的面貌:皆为水墨,有浓、淡、干三种不同墨法的作品,山形枯瘦奇特,石多树少,空间怪异,境界荒寒,与草木葱茏的江南山水迥然不同,也不似苍拙厚朴的陕西景观。景色是幻想的,气息是南派的。画法与风格,可以看到紧密、松秀、奇异、平淡、清幽、浓厚的变化,并非摹仿前人,没有西画痕迹,不同于流行样式。第二阶段的作品,以写生为大宗,集中体现在《江南系列》《太行系列》中。何加林写生主要采用对景落墨的方式,个别尺幅巨大之作根据写生加工。在这一阶段,也有少数作品如《白云浮江》《幽谷山庄》等与写生无关,它们讲究结构性,与真实景象有很大距离,生拙枯涩,精神气息与第一阶段作品遥相呼应。
写生完全改变了第一阶段作品奇幻、孤峭和冷逸特征,变得真实、具体、亲切、生动。一个画想象空间,一个画眼前景物;一个突出主体,一个突出客体;一个要求景物适应画法与风格,一个要求画法与风格适应景物。传统山水写生大抵是目识心记,略勾小稿,回到画室才落墨完成;20世纪以来的山水写生借鉴西法,对景作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李可染——一方面坚持对景落墨,一方面又强调主体加工,使写生具有创作性质;一方面放弃传统程式性画法,从对象的形质特点寻求新画法新程式,适当引入西画方法,赋予作品更强的真实感、丰富性,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发挥笔墨语言的表现力,维护中国画的基本特征。同时代一些老画家也重视写生,但他们没有西画根基,不放弃旧的笔墨程式,摆不脱“旧瓶新酒”的矛盾。李可染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对中西绘画都有较深刻的理解,兼能中西画法,有相当好的笔墨功底。但是,他的众多追随者却相对逊色,鲜有获“出蓝”之誉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呢?那原因,是追随者们虽有造型能力,却弱于笔墨功底,深受写实观念束缚,作品摆不脱“写生状态”:有过多模拟生活原型之弊,缺乏山水画应有的超越性和笔墨韵味。一些人照搬李可染的方法,又流于新的摹仿。新时期山水写生有很大突破,但大抵摇摆在上述两种倾向之间:或者模拟山水原型,失之过实,或者用既定画法去套对象,得不到自然的新鲜与生动。何加林采取对景落墨方式,沿着李可染的路线,追求描绘的新鲜、生动与丰富,努力再现江南景色的湿润和秀丽,但他对笔墨的认知、所经受的笔墨训练和作画的文化环境,与李可染及其学生大有不同。他更强调笔墨形式的独立性,更重视个人表现的自由。因为笔墨功底好,他没有拘于“写生状态”,没有那种连环画式的叙述性,没有丢失中国山水画所特有的诗情画意和笔墨趣味。他像李可染那样根据对象的特征探索创造新的画法,又没有像李可染那样一概将传统程式放弃,而是部分地融入,在不影响生动描绘的同时保持笔墨的独立韵味。和李可染写生相比,他采用的笔法更多,风格更趋精致。何加林比李可染更突出水墨情致,而又不失写生的真实与生动。李可染写生孕育了其凝重拙厚而深秀的山水风格,何加林的写生透显出其清隽、秀逸的气质,却与他的非写生作品保持着相当的差异。李可染写生探索在47岁以后,何加林画写生始于38岁。李可染对景写生的探索是开拓性的,何加林的对景写生推进了这一探索。
我作上述比较,是想指出,在李可染这样的大师之后,年轻一代仍能有所作为,即便在他最有贡献的写生方面也是如此。何加林的努力启示我们,山水写生不仅可以像李可染那样通过摆脱程式束缚而获得新的活力,也能够适当地借助于传统程式,把掘取造化源泉与充分的笔墨表现在更高的层面统一起来。在我看来,何加林的方式,在中国画教学中更具普遍价值。
何加林说,写生使他感受“有”,获得“实”,以后可能会“化实为虚”“化有为无”。“有”与“实”,可以解释为造化自然所赋予的充实,画面的生动与丰富。“虚”与“无”,可以理解为对具体景物的超越,画面的意象性和形式化。事实上,何加林同时兼能“虚”与“实”,“有”与“无”,可以轻松地出入于两者之间。只能“实”而不能“虚”,是近代采取西画方式写生的画家的不足,只能“虚”而不能“实”,是拘于传统程式的画家的缺憾。
何加林说的“化有为无”“化实为虚”,无疑指向了山水画的精神性目标。尉晓榕说,何加林在艺术上“是一个精神孤行者”,“他以现代的构成原理为依托,以完全的个性语言寻求一派荒寒的造境”,并从中“淡出孤峭的情绪”和“孤高不群的气度”。尉晓榕的文章写于1999年夏,谈的是何加林第一阶段的作品——它们确有“孤峭”特征。但在第二阶段的写生作品中,“孤峭”隐退,变得“山光水色与人亲”了。何加林是杭州人,5岁随父母到陕西,在西北山乡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那正是“文革”期间。他第一阶段的重要作品,如《秋气嶙峋》《汉中古道行》《华岳山魂》《楫云问山图》等等,都取材于关陇景色——不是真实的写生,而是记忆和想象。对山川的记忆总是和时代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作品的枯淡、荒凉、奇幻和遥远感,不免交织着画家记忆中的痛感和迷茫。加林是在可人的江南追寻这些记忆的,江南特别是杭州就成为关陇记忆景色的隐形对照。反之,当他作江南写生时,记忆中的关陇景色又成为江南景色的隐形对照。前者的苦涩、杳远和孤峭,后者的亲近、温霭和秀美,就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反差既源自不同的景物,也与不同的心境相关。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两种风格不同的作品也有共同之处,即笔墨语言的秀逸清隽,这秀逸清隽来自何加林所学的文人画传统,也根源于他的气质个性,或者说正是如此这般的气质个性选择了如此这般的笔墨语言。人的气质个性很难改变,思想、感情、心理一定随着年龄、环境、知识、经验的变化而变化。何加林作品在今后的发展,也一定受这两个因素的制约:或者偏向第一阶段的孤寂与幻想,或者偏向第二阶段的亲切与生动;可能在两者间折中,也可能交替出现类似的两种倾向。
郎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