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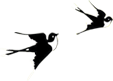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何士扬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何士扬 > 艺术作品 时间:2017-03-27 03:29:15
艺术精神的价值体现,是艺术家对具体生命根性的发掘和把握,并通过艺术作品,使这一根性在自由生发和尽情阐释的过程中,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文化产生某种影响,而得以实现的。这种影响对于具体的社会进程和人生轨迹,既具有正向的顺承作用,也有反向的内醒动力。在思考有关艺术是如何反映时代与社会的问题时,徐复观先生曾这样写到:“艺术是反映时代、社会的。但艺术的反应,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顺承性的反映;一种是反思性的反映。……顺应性的反映,对现实有如火上加油。反省性的反映,则有如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中国画的精神境界,是在中国文化的长期熏染下得以生发的,中国文化“内向”的特质,使得中国画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发挥得更多的是“清凉饮料”的作用。这种作用既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性格体现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价值所在。
一直以来,学界围绕“笔墨”的有关争论,实际上是分别取法于中西绘画不同理论体系的学者,对于中国画的不同“解读”而引发的学理争论。往深里看,这或许也是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冲突在美术界的又一次显露。如果仅从学理上分别审看,双方取法的路径各异,目的地也不尽相同,且如果皆能自圆其说,本来并无“对与错”可言。可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画发端、衍生于传统的中国文化土壤,自古以来有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和“宇宙观”。中国画的文化价值在其历经千年之久的有序传承中,早已获得了应有的肯定和确立,并在历代不断获得了演生与发展。自古以来,中国画的“生命系统”一直伴随着相应的文化环境,沿着其自身的“天道轨迹”循环往复并健康演进着。然而,近一二百年来,西方文明在强大的物质基础的护卫下,以救世主的超强姿态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同化和摧毁了无数的古老文明。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国文化也不能幸免地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中国画作为传承中华智慧的“明德之体”,其传统学理在传承中的作用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误读”和“肢解”。而回顾历史,这种“弱化”、“误读”和“肢解”的过程,又往往是伴随在西学理论对于中国画视觉满足的每一次“强调”和“解读”之后加速发生的,这种更多着眼于对视觉满足的“科学”分析,或许在局部上对于提高中国画的“造形塑造力”不无补益,然而,它却在总体上打破了中国艺术精神“境生象外”的“超越”理想、打破了中国画有关物质与精神的“生态平衡”。它不仅“肢解了”中国画独特的价值体系、“改变了”中国画的“天命之性”、最终也“弱化了”中国画存在于世界的文化意义。如今的现状是,学界已经逐步习惯于用西画的学理价值品评中国画。尽管情绪和直觉告诉我们“笔墨并不等于零”,但是,在西洋文化依然强势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辩不清我们的学术方向了,于是“笔墨”开始成为了“问题”。
如果说,近百年来中国画的传承是在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那么,与山水、花鸟画遭到冷遇相比,人物画则更是曾经长期处在接受西学学理“科学”改良的背景下,寻求着它的生存权利。尽管近年来呼唤中国画传承、回归传统学理的呼声时有出现,对传统人物画“线描”的研究亦渐渐成为了另一种热潮。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一拨研究,其出发点大多依然停留在对所谓“绘画语言”的研究,我们还没有看到以传统学理为根基的当代拓展,成为我们谈论中国画学术话题的重要语境。
尽管如此,当我们回顾近百年的中国画演变历程时,我们还可以十分骄傲地看到,近、现代的陈师曾、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一批老一代“知行合一”的学者型画家,他们在面对时代变迁时仍然表现出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和自豪、对于中国画学理文脉的维护与坚持,正是今日我们探求中国画学理价值、寻求中国画当代拓展所应推崇的榜样、所应传承的品格。陈师曾以生命之热情守护与宏扬传统中国文化和对花鸟画中和之美的挖掘;黄宾虹以修养之深厚对传统学理的维护和对祖国山川雄浑之美的勾勒及秀润之韵的表达;齐白石以艺术之真率对生命根性的发掘和万物之象的把握;潘天寿以君子之品操对民族艺术的守护和担当并使花鸟画在他的手下开放得更加刚强与大度等等,都已成为中国画百年演进的经典案例,值得我们再再回味。尤其是黄宾虹先生,其超然的学术思想和超越的精神境界更是值得我们敬佩与继承,特别是在面对当时十分纷繁复杂和极端追功逐利的学术环境时,他仍然能以自由的心灵和超拔的思想,固守中国画的价值取向,并且以独立的视角使中国智慧在其有关中国画的,法、理、道的研究和阐释中,不断得以生发和现显,使之获得历久而弥新的精神力量。历史既无情又有情,尽管时间过去不久,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百年的中国画史将不可能遗漏陈师曾、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这四位大师的芳名。而且,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是我们今日重思中国画学理价值和寻求中国画当代拓展的精神向导和学术基础。
在面对西方文化强烈冲击的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画为了救亡图存而经历的长时间坎坷与磨难、心酸与尴尬,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扭曲和“肢体”伤痛。如今,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中国画必将在未来的旅途中,一方面通过打通自身的学理“经络”,实现与传统智慧的重新对接;另一方面通过克服特殊年代所遗留的思维惯性,恢复中国文化有关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心态。以便在面对“图像时代”的种种诱惑时,仍能以“橙怀观道”之心,努力复现中华文化的“本体之明”。 百年的思维惯性和知识断层或许需要用足够的智慧和耐心才能获得真正的超越,但寻求超越与尝试修复的努力本身或许就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另一种体现。
在当代背景下,我们尤其不能设想的是,当一个个体的生命之躯,在遭到外部力量的长时间“肢解”之后,当它已经经络不畅、支体移位、身心搬家之时,我们还在指望它保有健康的体魄,还在指望它能尽健康生命的一份责任,指望它能显现健康生命的同等价值。同样,当中国画的“综合之体”仍然面临时代变迁的考验之时,在它的价值系统尚未完全获得康复之际,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使它立定根本,做“固其本、复其性”的努力,使之避免夭折。接着,才能希望它以完整、健康的生命之躯,迎接未来自然之力“四时生杀”的种种考验,实现它作为一个健康的生命之体,由小变大、由幼变老的生命演化。
“新与旧”、 “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当这些词汇以学术的名义幻化为无形的魔咒,紧紧地缠绕着人们的思考系统,成为横亘在文化进路面前的价值标的时,我们将无暇回望我们的传统,无缘获得中华先哲智慧之光的照耀,因而也就无法传承中国画超越万象的本体动能。在这个物质利益至上的特定年代里,如果我们不修持理性的金刚之剑和智慧之心作为护卫,我们将很容易陷入钱穆先生所批评的“浅薄的进化观”思维惯性之中。使我们全然忘却了自己的“天命之性”,忘却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规律,而迷失在眼花缭乱的“视觉盛宴”之中,在色相迷离的欲望之海里尽情满足人们的饕餮之心。而这一切都是与中国画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的。所以,本文认为“夫欲壮其枝叶,必先固其根本”, 国画形态的当代拓展之路必须从回归传统学理起步。
最后,让我们记住黄宾虹先生在《致治以文说》一文中的教诲:“今则东方文化,骎骎西渐,而中国学者不深猛省,怵他人之我先,将自封其故步,非确加诚实之研究,无以保固有之荣光。凡我同志,盍兴乎来!”
何士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