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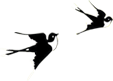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何士扬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何士扬 > 艺术作品 时间:2017-03-27 04:18:37
“雍言馆”作为我的画室堂号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十年来,我以补课的心态在这里读书和画画、喝茶和会客。
“雍言”二字是零三年客居电脑中心时,与耀鹏兄在玉皇山下聊天时取的。“雍言”我取它从容和谐的意思。“雍言馆”作为画室堂号随我搬迁过两次。零五年起安顿于现址。
环顾四周,“雍言馆”的任何一支笔、任意一张纸或一个茶杯对我而言都具有特殊的涵义。因为在长期的交往中,我读懂了它们的脾性,他们也知晓了我的习惯。
画室由并不太大的三部分空间组成。第一部分集客厅、茶寮和写作间为一体,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在不需要外出的日子里,用过早餐之后我总要在这里磨蹭半天。先用白瓷扣碗泡一小袋茶,使铁观音特有的清香在口腔和画室里轻轻地弥漫。音乐如果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响起,一天中最幸福的发呆状态常常就此到来。沙发边是我的电脑桌,许多论文和随想大都在这里写就。
音乐通过两米宽的大门框从画室里传出。画室是“雍言馆”的主体部分,面积二十五平方米左右。它的重要器物是大画桌、大书柜和大画板。平时我习惯于象画壁画一样站着画画,所以大画板是由两块特制的铁板镶嵌于墙体之上的。站着画画一方面是为了保护颈椎,避免职业病。另一方面能够提高用笔的灵活性,避免人物画平看和竖看的视觉误差。
长期以来,我逐渐养成了在大画桌上翻书的习惯,所以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画册、字帖和书籍。文房四宝是不可或缺的器具,画桌上至少同时摆放着十几方大大小小的古今砚台,十几锭墨;陶瓷、水晶和黄花梨笔架上分别搁着近期常用的毛笔;不同材质的几个笔筒里,装满了我认知毛笔的心路历程。
老花镜和一颗小松树子、放大镜和一对剔红漆轴头、手表和一对把玩核桃,几串佛珠以及之前从日本淘来的小小砚台,同时被收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红木多宝盘里。多宝盘边上还有一方小锡盘,盘里装着几个老印泥盒和一个小葫芦。小锡盘位于画桌的前端,它的后面是一块端砚老坑石,前头隆重摆着妻子刚刚送我的一盆观音莲。
宣纸放在官帽椅左侧的小台柜上,除了一卷已被裁成手卷的五十年代老纸之外,更多是我的特制专用纸。在对纸的认识上,我十分认同吴湖帆先生“生宣纸盛行而画学亡” 的观点。
斜靠在大书柜边上的几卷丈二老鸡球纸,是我几年前为了画《智者大师说法图》淘来的。大书柜在画桌背后和左手边,它们的连接处是博古柜,上面有我喜欢的几张老画和一些把玩老器物。层层叠叠的书册由书柜堆到了地上,一直到沙发边。大画板在画桌的右边,它与大书柜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同字壳。大画桌坐北朝南,画累了我有时会坐到画桌前的老椅子上看阳台。老椅子是清代的,靠背上的螺钿镶嵌得相当考究,看上去比坐上去更舒服。
阳台大约十来平方米,在画室的正前方。东边种植了十来株大大小小的盆栽,由天台山请来的兰花年年都如期开放。阳台正南边的两把小木凳之间,架着一枝楠木,楠木上摆着一块老的木雕匾额。冬日的午后,我往往泡一壶岩茶坐在阳台的小藤椅上,欣赏木雕上的神仙们在祥云和楼台间自由穿梭。
牟宗三先生认为,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对“人性之常”与“自然之常”的领悟,“雍言馆”十年来之于我的,或许只有领悟此一领悟的感慨罢了。
以“雍言况味”作为画展的题目是我自说自话随想随写的结果。一大堆关于画室的文字,肯定说明不了什么。“雍言馆”主人的生活景况和人文情味还得劳烦有缘人通过品画获得。
在时下极端喧嚣的氛围中,一位中国画学习者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面对社会和展示艺术?谋生成就和艺术成就对艺术家而言哪一个更重要?尽管一篇不拘篇章的画展自序是难于厘清许多问题的,但我还是希望在这不成序言的序言里,已经一定程度上表显我的姿态了。
何士扬
癸巳三月三于雍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