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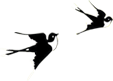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何士扬 > 艺术作品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家 > 何士扬 > 艺术作品 时间:2017-03-27 03:32:58
时间:2009年4月15日 下午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二楼(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毕业展现场)
对话人物:毛建波、何士扬
毛建波(以下简称“毛”):这次浙江省重大题材的美术创作,除了由政府拨款收藏这些作品外,还希望将整个创作过程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我想以访谈的形式可能更利于将创作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以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出来。
你我相交已久,平时交往较多,虽然这次你参加重大题材作品的定稿我是借博士毕业生作品展的机会才真正看到,但在我们之前的几次相处中,都有听到你谈及对于这次创作主题的看法,而且几乎每次都是谈着谈着就说到了国清寺、智者大师等等——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似乎你已经完全投身其间了。
何士扬(以下简称“何”):是的,昨天开展的时候有几位老师也跟我这么说。我这几年可以说是沉浸其中。
毛:人都是有阶段性的,有时候可能要三五年时间才能做好一件事情。而且,不是说作品出来就是事情完成了,更重要的是思想、经历的积累和转变,包括绘画作品的题材甚至是走向可能也会随之而变。在厦门大学期间,你主要关注都市生活,以彩墨画了都市人物系列。回到中国美院以后,你也有了些改变——更多地画一些水墨的文人、仕女等题材。我还为此写过一篇《折返水墨》的小文。而这次你画了高僧大德。那么,这次创作的主题是组委会安排的,还是你自己的选择?
何:这说起来也是有一个因缘际会的过程: 2003年10月,由于参加在杭州举办的“尖锋水墨——中国画名家邀请展”的缘故,我和参展的二十来位画家由组委会组织来到天台国清寺游览参拜,期间得到了允观法师和齐梦初先生的热情接待。国清寺古朴的建筑和参天的古木,其独特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对我形成了强烈的吸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感触。而且,可能是那里环境好,含氧量高的关系,我们在那里走了一圈,竟然不觉疲惫,反而神清气爽,这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真正起念要以画笔表现智者大师开创天台宗的事迹,是缘起于我与林海中、张伟民的一个联展,展览期间正值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杭州召开,所以展览期间有不少宗教界的人士前来观展。自此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有了交往,从此,开始了我近五年多来亲近国清寺和天台宗的缘分。具体说来,当我领到了驾照并开始练习开高速远途时,第一趟去了绍兴,第二趟就开车去了国清寺。到了那里,有许多新老朋友都说:“我们正好去看过你的展览……”,并对我的画有所称赞,就这样聊起了画的事情,期间,我主动表示可以为国清寺画张画,是允观法师第一次为我介绍了智者大师的生平事迹,并送给我《国清寺志》一书作为参考。当晚,我在国清寺宾馆第一次阅读《国清寺志》,当读到灌顶大师撰写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时,即被大师一生“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旃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驱,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不可称数。”的事迹所震撼。
回来以后,我就开始了画这张画的准备,当时又正值重大历史题材开始布置任务,让每个参加的画家选两个题目——我以为只能选一个,就选了智者大师开创天台宗这一主题。其实,当时有其他的画家也选择了这个主题,但他们知道我已经在着手研究天台宗的历史——因为那段时间我跟朋友聊天提及过这件事情——有的还很友好地给我打来电话,意思是你要画这个主题我们就让路了。所以,我始终认为由我来画这个主题是一份因缘,也是一份责任。但是,当我真正投入了之后,也就逐渐地变成了兴趣,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主题中蕴涵了很多很多内容,包括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人对待文化的态度等等。
毛:之前你也画过一些传统题材,其中也会涉及一些佛道人物,但我印象中你真正深入描绘佛教题材应该就是这次吧?
何:对。之前是有画过一些菩萨像,但不多。可以说,就是这张画,让我真正进入了文化和学术的层面去表现佛教人物题材,也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
毛:当选题确定以后就要开始搜集资料:一方面阅读文献资料,一方面采集图像资料。我估计图像资料应该不太有了,或许国清寺可能还有一点,那么文献资料又是来自何处呢?
何:天台宗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那里保存有一些相关的文稿和唐代士大夫的画像,也有很多相关文献,所以我搜集了一些日本的书籍。另外,也看了日本创价学会池田大作写的一些关于天台山的文章,尤其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今天,我更加赞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观点:“天台及其思想……会给现在正在面临崩溃危机的西欧近代文明体系带来一种新的觉醒”。国内方面,就是跟天台宗的法师去交谈——国清寺和杭州佛学院等几个地方都能找到天台宗的法师。但是,最主要的文献资料还是来自于天台宗的五祖——章安大师,又称“灌顶大师”——他是智者大师的弟子,对天台宗有非常大的贡献,他写了一篇智者大师的传记,叫做《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写得非常生动。我对照着他写的智者大师的生平和一些细节,归纳着画了八张画。
毛:就是类似佛本生故事里描述释迦牟尼成佛一生经历那样的图吧?
何:对,佛家有释迦牟尼的八相成道图,“八相成道图”后来成了专有名词,中国人好像对“八相”有些避讳,因此我一般都说叫智者大师的“法相”或“德相”,或是“八图”。为了感念智者大师一生的功德,我早在两年前就已发愿心,除了认真完成《智者大师讲经图》的创作任务,还要为智者大师画八张德相,来颂赞大师的功绩。从客观来说,我画这八张画也是在为重大历史题材的大画而作的准备,因为,只有深入到智者大师的人生轨迹当中,才能了解其中的精神。这里面还有段因缘:智者大师的老师是南岳慧思禅师,他拜慧思禅师为师的时候是23岁,而章安大师拜智者大师为师的时候也是23岁。正是经过这非常优秀的师徒三代人的传承,才创立了佛教真正意义上中国化的第一宗派。如果将天台宗的传承脉络再往上追溯,慧思大师的老师叫慧文禅师,而慧文是传自印度的龙树大师。智者大师得道于慧思禅师后,主要活动于天台,所以称为“天台宗”。可以说,智者大师是天台宗实际上的创始人,但其学术渊源应该是由龙树、慧文、慧思、智者,再到章安,这五位禅师合称“天台五祖”。
佛教中国化至少经历了三个时期:首先是汉朝、东晋至南北朝的融合时期;其次是隋、唐的再创造时期;最后是宋及以后的儒化时期。智者大师生活在陈、隋之间,是再创造时期的开拓者。天台宗的思想事实上是站在了当时中国众多思想的融接点上,她融接了道教、佛教、中国文化等多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和久远的影响,所以被称为第一个“中国化”的宗派——被称为“宗派”是需要符合几个条件的:有自己的思想文脉、自己的师徒传承和自己的祖庭道场。其中,祖庭这个条件是由智者大师选址、设计的,最后由章安大师“依图造寺”完成的,直至此时才算真正创建了一个宗派。换句话说,佛教是外来文化,只有当它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之后,才能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产生影响、起作用。所以,我想正是因为如此,这次的组委会才会把“智者大师讲经图”作为重大题材的主题之一而提出来。
毛:是否可以这么说:你之前画的八张画实际上是选择了智者大师一生中最重要的八个节点?多数人对于智者大事的生平事迹不太了解,你可否简单地解说一下这八个节点?
何:对。第一幅《龙兆出世》——画的是智者大师的出生。据记载,智者大师出世时有种种奇特现象,母亲怀孕时常梦见五彩祥云,又梦见白鼠入肚,卜者称是白龙入腹。此外,颜真卿形容他为“尧眉舜目”:“尧眉”,据说尧的眉毛是五彩的,我想智者大师眉毛的颜色可能跟寻常人也不太一样;“舜目”,则是因为智者大师的双目跟传说中的舜一样,是一双重瞳眼。还有历史上传说大师小时候是“坐必面西,卧必合十”。所谓奇人异像。这些画里都有一定的体现。
第二张《遥梦天台》——讲的是智者大师的佛缘。他小时候记性很好,别人给他看的佛经,他几乎读一遍就能背诵。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的父母怕他会出家,就把他关在家里,不让他接触佛教。但他“一日正拜佛时,恍梦山临大海,僧居上招手”。后来在天台“定光草菴”,定光禅师和智者大师共同印证了这一前缘。
第三张《大苏妙悟》——据记载,智者大师前往南岳向慧思禅师学习禅法,经过七年的日夜精修,在大苏山读《法华经》之《药王菩萨本事品》“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豁然开悟,亲见灵山法华圣会俨然未散,悟得法华三昧,得初旋陀罗尼,从此以后,辩才无碍。世称“大苏妙悟”。
第四张《瓦官弘法》——当时智者大师前去向慧思禅师学禅,师徒二人一见十分契合,慧思禅师说:“昔在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遂,今后来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宿世因缘的。后来,智者大师就住大苏山潜修七年,学成以后大师在南京瓦官寺讲经八年,宣扬天台宗的根本典籍,为日后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记载智者大师讲经非常精彩,而且影响很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的逻辑性、思辨力和思想深度都很卓越。而且,我估计他的声音也很宏亮,据记载,当时常有上千人同时听他讲经,而即使是在最外围的信徒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此外,智者大师通过讲经也确立了他在佛教中的地位:八十几岁的大和尚都赶来听他讲经,而且折服于他,拜他为师。后来连陈朝的皇帝和太子也都来拜他为师,加上后来的隋炀帝也拜他为师——所以后人也称他为“三朝国师”,地位在当时非常崇高——甚至有的大臣为了听他讲经,连朝都不上了。但是,此时的智者大师并不高兴。他认为,虽然听经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得道的人却没有增加——古代的大德都是这样,弟子没有进步他不会怪弟子没有悟性,而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需要继续地修行。并且,当时是陈(朝)隋(朝)之间,军阀割据,连年战乱,百姓的生活都很艰苦,智者大师很想救众生于水火,把真相传于众生。此时,他想起自己从小就有天台山的因缘,那么他的大道可能就在那里。于是,他就不顾皇帝的挽留,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带了二十一个徒弟到天台去苦修。在此之前,他的老师告诉过他一句话:“若不自证,何以度人?”所以他就秉持“知行合一”这一信念继续修行——这就符合了中国文化所要求的,也即是后来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
第五幅《华顶降魔》——讲的是智者大师在华顶潜心修行,直至达到了他修行的第二个境界。智者大师修的是头陀行,修行悟道到了一定的境界就会有天魔或化为妖魔鬼怪,或化为亲人好友等等前来干扰,一旦心有不定,为之所动,心魔便伺机而入,而智者大师不为所动,即降魔,进入了绝对止观境界,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
第六张《金雀来仪》——讲的是智者大师很重要的一个贡献。他在浙江沿海五百里提倡放生——实际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提倡生态平衡。有一天,在寺院的上空出现了很多的黄颜色的鸟,又称金雀,一直在房顶久久徘徊不去,所有的和尚都出来看,有的就问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大师说:“江鱼化作金雀,来此谢恩耳。”天台宗提倡放生是不遗余力的,据说,佛教提倡放生在印度就有,但是放生池与寺院建筑融为一体的结构,与智者大师大力提倡放生的历史有关。
第七张《寺成国清》——讲的是智者大师初到天台山时,正觅求可以栖修之处,遇到一个老先生——也有说是定光法师——跟他说;“山下有皇太子基,拾以仰给,“寺若成,国即清”。智者大师努力一生,又亲自描绘寺院式样,并在圆寂前遗书致杨广,促成“依图造寺”。梵宇告成,国清寺遂成为天台宗祖庭。
第八张《东土释迦》——画的就是一个结果:智者大师一生勤劳精进,著作丰富,有“天台三大部”“天台五小部”等,在大师及其弟子的努力下,天台佛教事业终于发展成为自东传以来,最早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智者大师被尊称为“东土小释迦”。由于前面几幅都是四字为题,所以我就把“小”字去掉了。“东土释迦”这个称号实际上就是颂扬他对佛教中国化所做出的功绩。
毛:这八张画很生动,你有没有考虑过再画得大一点?
何:现在暂时不会,以后有机会再说。之前也说了,为了感念智者大师一生的功德,我发愿心要为智者大师画八张德相,来颂赞大师的功绩。今年是智者大师诞辰1470周年,我也已于近日达成了心愿。为了感谢国清寺对这次主题创作所提供的种种帮助,我将“智者大师法相”共八幅精装成套,送与国清寺永久保存。这次要展览,我是作为《智者大师讲经图》的系列作品,向他们借过来展一下。如今,我又将八幅“法相”及有关介绍智者大师和天台宗的文字内容汇编成册、结集出版,为的是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智者大师的事迹、感念智者大师的功德,更是我对大师心存敬意的真诚表达。
毛:佛教有这样的传统——往往把有特殊意义的事迹等制成壁画。这几张画是否也会放大成壁画呢?
何:这个要看他们是怎么打算了。国清寺造了智者大师的雕塑,边上的壁画怎么画还没有想好。如果他们需要,我会愿意去做的。
毛:国清寺应该做这么一个讲堂,把智者大师的雕像放在里面,墙上再画些相关的壁画。
何:其实雕像已经做好两三年了,但他们一直都没有想好壁画要怎么画。
毛:刚才你简单介绍了八张画的涵义,其实等于已经将智者大师的主要经历梳理了一遍,而《智者大师讲经图》的意义其实也包含其中。那么你为什么没有画智者大师生平中一些轰轰烈烈的场景,而是选择了相对平实的弘法的场景呢?
何: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其一,这次是画重大历史题材,因此我们表现的应该是历史上已确定的史实,而不是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字传说,这也是这次创作的主要着力点;其二,讲经弘法是天台宗这个宗派最重要的特点,而智者大师的讲经水平又是天台宗之中最高妙的。有传说形容,智者大师讲经的时候,经堂上空会有天女散花,又如莲花盛开,刹那芳华,芬芳无比。
毛:要表现天台宗这么宏大的题材,就有一个角度的问题,最终你选择了以“讲经”这个来表现。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重大历史题材组委会历史组的专家学者们有没有提出过建议呢?他们认为以“讲经”作为着力点是否可行?
何:实际上,原先我的确是打算将智者大师的一生画成八条屏的,但是专家们觉得这其中可能有传说的成份存在,还是应该画得更现实一点。他们这么一提,我也觉得很有道理,那么就选择了“讲经”。因为,讲经是天台宗和智者大师本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样归纳很好。
毛:那么在实际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又提出过什么建议呢?
何:当我决定下来画“讲经”之后,他们也觉得很好,这样是对的。然后,我画出的草图——就是挂在大画边上展览的那张——他们看了也觉得不错,但是里面的房舍似乎不太像人们印象中的庙宇,比较像一般的民间房舍,所以他们认为应该画个大的殿堂。其实,原先我还考虑过把讲经的地点画在室外,因为天台山有一块“智者大师讲经石”的。但专家们还是认为画在殿堂之内会比较有气势,我想想也是有道理——正常的讲经是比较庄严的,大部分时间都应该在室内——就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你要画殿堂,然后又要在殿堂中画很多人在听讲经,这就很有些难度了。因为,传统的佛教题材画往往会把主要人物画得很大,边上的人物处理的很小。我们既然以现实为主,那么就不可能做这么夸张的处理。所以,我还是慢慢地琢磨着处理一众人物的大小比例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环境的处理问题,我的方法是把树木、树冠的朝向往中间放,那么整幅画的气息就会比较集中,也会把人的眼光往中间吸引。所以,昨天展览下来也没有人觉得这幅画会有主题不够突出之类的毛病。
毛:你这幅画把人物推到了相对后面的地方,在画面的前方画了放生池、台阶等等,又把树木比较均匀地放在两边,这样是为了形成比较中正的构图?
何:对。因为专家们当时给的意见也是如此——既然画庙堂,那就要画得中正,而且画庙堂是要有石台(阶)的,没有石台(阶)的庙堂是不成立的。接下来,我又在前面画了莲花池,或者说是放生池,这样的处理让整幅画显得比较端庄,符合人们印象中对于庙堂的理解,所以大家也都接受了。
在建筑风格方面,隋唐的建筑风格相差不大,尤其是唐代早期的建筑,跟隋朝的几乎一样,所以,在建筑和服饰等一些配件方面,我还是做了一些功课,基本参考了唐代的一些资料。
此外,由于画了亭台、石台和庙宇,线条就比较多,所以边上的树木和赶来听经的人实际上起到了调节画面动静关系的作用。
毛:宗教壁画通常都有比较丰富的颜色,如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等,而你怎么就考虑用难度最大的勾勒的方式来处理这幅画的呢?
何:原因有几个方面,跟我对艺术的认知有关系。
其一,由于要准备博士论文,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比方说,为什么我们的纸会越画越薄?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国就有了漆画,也很早就发明了矿物质颜料等,但为什么到后来绘画的载体会由布变绢,绢变纸,越来越薄了呢?我想,其根源是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往往在物质繁盛的时代,中国人会想要通过减低物质对视觉的冲击,来提高作品所蕴涵的精神能量。为什么隋唐的线描很厉害?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耳朵聋了,他的眼神就会说话;如果哑巴了,他的眼睛、耳朵就会特别敏锐。此外,最近我还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从古至今我们的图式越来越丰富,但其中的精神含量却越来越少了呢?潘天寿先生说过,中国画要跟西洋画拉开距离。因为,中国画生存的“生态系统”和“宇宙观”是跟西画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表现的方式也应该不一样——潘先生实际上是很注重精神的。《金刚经》中有句话叫做“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就是说,所有的“像”都不是真谛,只有到“诸像非像”,提高到超越物质层面的理解,才能“见如来”,即得到真相;儒道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它们提倡“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就好比吃东西要尽量丰富,因为每种食物都含有不同的有利物质,所以菜色越丰富对身体越好。但是你喝牛奶不代表就变成牛,还是人,其中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吃进去的东西“消化”掉,为我所用。所以黄宾虹先生在画面表达的时候,就把“消化”所得提升为很简练的东西:所谓的“提、按”,所谓的“运笔适度”,所谓的“转、折”……笔墨精神跟画者心理节律曲折的契合,在这里面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中国人讲“意境”、讲“神韵”,一开始就讲“取法乎上”。我们可见,每一次西学对中国画的解读都是强调物质的层面,其对所谓的视觉效果和所谓的提高造型能力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它打破了物质和精神的平衡,也就是打破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每一次全国美展之后,大家都会很失望:中国画怎么画得不像中国画了?其实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其二,我们画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不仅是为了反映历史,在取法上也要有我们的高度。
其三,既然唐以前以勾勒法为主,我现在要反映那个时代的内容,就应该用勾勒法,否则可能与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联想会有出入。
正是由于这三个层面的原因——学术层面的思考,反映题材的需要和历史的积淀——我选择了一点颜色都不上。这里还暗含了佛教的意义,孔子曾评价佛教说:“西方有圣人焉,其教以清静无为为本,不染不着为妙”。因此,为求净雅庄严之境,无论人物、庙舍、石台、树木或荷莲皆不着一色、不渲不皴,正合了所谓的“不染不着”。
毛:你刚才说尽量想取法高古,以唐人的画法来表现唐代的史实,以求画面与时空的对接。
何:对。我感觉自己还是尽量取法唐代的画法——有没有做到是另外一件事。此外,我还看了不少唐代及唐代之前的资料,参考当时的服饰和造型方法等等。当然就这张画而言,它有自己的生态性,比如说我画的树法与衣袂的笔法、亭台的线条就要有所区别,形成这幅画自己的一个系统,包括用笔的方圆、用笔的速度、运笔的提按和运笔所蕴含的造像等等。但总体而言,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自己还是在一步一步地追古的,甚至感觉自己还是跨越了以前的一些认知。我的导师吴山明老师也跟我这么说:“你还是应该取法高古。”我觉得现在是对中国画的价值观进行重新地思考的时候了,所以自己这几年也在往这方面走。
毛:你创作这幅画有没有受到宗教绘画的影响?比如说山西永乐宫壁画之类。
何:永乐宫以前去过,直到现在都还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我这次创作跟那个倒是关系不大。因为永乐宫的壁画实际上还是填颜色的,它的用线基本上还是为了填颜色做准备,用的还是铁线描、游丝描那一类。而我在提按上还是讲究用 “吴带当风”的那种感觉——吴道子的着色也是不多的,所以他的《嘉陵江图》可以一天画出来——“兰叶描”一类的提按多,表现力很丰富。
毛:你的另外一张草图上有一段颜真卿写的《智者大师画赞》,这段资料是从何取得的?
何:上面的文字是由国清寺提供的。
毛:就是这段文还在,但颜真卿的书法已经不在了?
何:对,字已经不在了,但是国清寺还留有一些颜真卿的碑刻,因为曾有许多文人墨客到过那里——这些都有文字记载——当时还是有很多文化人是很了解和景仰智者大师的,因此,也留下了一些记载大师生平的文字——《国清百录》即是如此,其中的大量文章,使我对智者大师的认知从第三人称的资料阅读逐步转化为第一人称的心理感悟。第一次阅读《国清百录》智者大师的文章时,我深深为大师的慈悲胸怀所感染,以至落泪:
在《训知事人》篇中记载,大师“出家三十余年,唯著一衲,冬夏不释体,上至天子,下至士民,虽有所施,受而无私”。要知道,智者大师当时是国师,皇帝也好,大臣也好,都送了他很多东西,但他全部都列为公物,并一一记录下来。智者大师只活了一个甲子,前三十年修行,后三十年弘法,得到了很高的尊敬,除了皇帝大臣,民间也有很多人送了他很多东西,但他仍然身上“唯著一衲”,更甚者是,他的衣服不超过三件。他说,每一样送我的东西都不是我的,是众生的,所以他几乎没有私物。
而在《给晋王杨广遗书》篇中,大师“生来所以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的深情表白,以及希望晋王杨广“加修慈心,抚育黎庶”的文句,都深深打动了我。我感到大师身为陈、隋国师,却能爱惜民力,公而忘私,过艰苦朴素的生活,堪称世人楷模!其慈悲为怀,为了济度众生、弘扬佛法、勤勉精进、天下为公的崇高人格堪令世人感佩!正是这样的人格魅力才能吸引那么多人……
随着对资料研读的进一步深入,在经历了一次次的震撼与感动之后,智者大师的圣相逐步在我的脑海里浮现:那是一位在***的年代里,为了教化和济度众生而努力一生的圣人、一位被世人尊为“东土小释迦”的佛学宗师。
毛:在我印象里,你最近几年的创作中,这幅画是最大的。那么像这种政府指定的历史题材,又有相当高的要求,在你的创作过程中感受最大的是什么?
何:收获最多的是——跟我学佛学一样——有件事情挂在心上,需要你去完成。最有意义的是,因为我要创作这幅画,所以必须去了解智者大师创立天台宗的历程,而我从此得以发现其中蕴藏的那种精神的力量,擦亮了我的眼睛,让我看世界、看历史的目光和角度有了一个很大的超越。我这两天总是跟别人说,人性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喜欢聚居。人一旦聚众起来就会生“俗谛”,就会产生攀比心,从而搅在无形的波澜当中。中国艺术精神是追求超越的,超越物质是提高境界的前提,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更为重要。要超越,就要求现代人要让自己偶尔“孤独“一下,这有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把眼睛和嘴巴的功能关闭的时候,耳朵会更灵敏——关闭外来的信息,排除外界的诱惑,内照自我,就会看到自己的内心,看到并了解自己的心性,是从事艺术、从事文化的前提。
毛:以上你说的是心灵方面的得益,那么此次经历对于日后你具体的创作方面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对你的画风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何:已经改变了。我的博士论文最早写的是“中西线比较”,后来写“十八描”,现在写“勾勒”,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我对事物本身的认识是在步步提升的——“比较”,是“像”的比较;“十八描”,也是“像”的研究;“勾勒”,则是兼具了“像”和“非像”的概念,已经进入了心灵的轨迹,进入到了对文化的思考,已经进入了对“道”的追寻……那么,不管追逐的结果如何,至少我“取法乎上”了,已经进入了这条路。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再走回头路,因为我已经走上了一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限于绘画范畴的驾驭之路,要走好这条路,更要弘扬它。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画家自我精神的需要,也是对社会的一种“交代”——我们画画是给人看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所表达的东西是对的,把中国文化的价值显现给更多的公众看。
毛:如果把你之前的绘画分为几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比较多的是画都市题材,用色彩的方式来表现;后来回到浙江以后,传统题材就画得比较多,用水墨表现;那么这次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是不是意味着你今后会比较多地着眼于用勾勒的方法表现宗教或文化题材呢?
何:黄宾虹说,画中国画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必须学勾勒法,画人物;第二阶段是画花卉;第三阶段是画山水,寻找变化。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找寻中国画的真正价值,黄宾虹说的这个次第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把中国画的笔墨的三个阶段一一概括了。那么对我而言,其根本即勾勒法——中国人说的“书画同源”从何而来?我认为是从“伏羲画卦”而来、从“仓颉造字”而来。“伏羲画卦”是绘画的“祖先”,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而在这两仪的相生相融中,万物才得以化生。黄宾虹先生说:“向左行者为勒,向右行者为勾”。这一勾和一勒是可以化生万象的,它是“众有之本”和“万象这根”,也是石涛“一画”之理的思想根源。如果你的一勾一勒没有进入这个思想轨迹,那么,可以说你对中国书画的渊源是漠视的,如不闻不问加上不用心,那你何以了解中国画艺术的真谛呢?这“一勾一勒”看似简单,但其蕴含的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起点、归宿点和精神之果,而这种精神之果恰恰是我们的艺术、绘画的价值所在。所以说,勾勒法既然可以化生万象,那么,它本身就是人物画的艺术之果的体现。我最近对黄宾虹倍加推崇。老实说,我从前不太看黄宾虹的,别人说他如何如何,我都闭口不言。现在我说,黄宾虹是得道之人!他的精神需要得到弘扬!所以,最近你们可能会经常听我说到黄宾虹。
毛: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结束后在新建的浙江美术馆会有个大型展览,与此同时浙江美术馆还有名为“神州国光” 的黄宾虹的大型展览。
何:到时我一定要去拜读。做黄宾虹的推广者,要尽可能地做他思想的推广者。因为很多人实际上是看不懂黄宾虹的画的,如果推广需要帮助,我愿意参加。因为,中国近代画家中,能够把中国文化理解透彻的画家,我认为黄宾虹当排第一。
毛:这件作品的创作应该说已经告一段落了,到目前为止,你自己觉得这幅作品还有没有什么遗憾,或者说末能完全实现出来的地方?
何:如果这算一个阶段,那么对于浙江启动这样的文化工程,我心存感激,它给了我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一种缘份,让我能够在这个阶段付出自己的努力,也得到了收获——就像我读博士一样,我对能够帮助我去读博士的人和事都心存感激。因为这次的主题创作,我去了解并画了智者大师,他对于我以后的影响必定会非常深刻,难以淡化。
毛:如果要你给自己的作品打分,你会打多少分?
何:我尽力了。画这么大的画,还坚持只用线描,不染不着——有好朋友劝我还是染一点色,但我还是坚持不染,我认为既然古人可以做到,我为什么不能?这张画我从春节一直画到现在,大概有两个多月,但是围绕着这幅画我大概准备了三年——其实一直在画一点、画一点,但总觉得功夫未到。到了春节过后,我觉得契机到了,才真正开始画,过程中没有打过铅笔稿,仅用毛笔底稿定位。我现在都是用勾勒法打底稿,因为用毛笔时的提按的效果跟铅笔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所传达的神韵也是不一样的。
毛:在此以前你有没有画过历史题材?
何:没有。
毛:所以第一次画就挑战高难度。
何:对,经历过之后觉得自己似乎从里到外都换了一个人,连看世界的方法都变了。
毛:回到这次的主题创作,我看到一个细节——你在莲花池的匾额上写了“妙法莲华”,这有什么涵义?
何:这个你问到点子上了,我倒是用了点心思的。这个原本是放生池,国清寺中写的是“鱼乐池”,那么画中要写什么呢?后来我还是决定写“妙法莲华”。因为,天台宗也称为法华宗,它最主要的经典也是从“妙法莲华”来的。从表面上看,“妙法莲华”与池中的莲花正好契合,但它其实是讲一种境界。如果是对于天台宗有研究的人,一看就知道“妙法莲华”这四个字正好点了天台宗这个题。
毛:能否认为你这张画已经得到了“妙法莲华”?
何:我自己肯定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整个过程我都努力了,对于帮助过我的人,我心存感激。